少年武士梦之马
戴冰 黔中书
喜欢冷兵器的人,大约没有不同时也喜欢马的,设若挥刀舞剑,盘弓发矢,而少了胯下矫健如龙的良驹,那威风,那杀气,怕只剩得下三分之一还不止吧。不过我喜欢的马,自然不是寻常那种垂头、大肚、短腿的马(滇、川、黔的马大都如此),而是军马。还记得第一次看到真正的军马,是六七岁时,某日中午随父母上街,途经贵阳一中操场,正碰上一队骑兵逶迤而出(估计是借一中的操场训练),蹄声得得,顺大路一侧朝火车站方向渐行渐远。我立在当地,如触雷电,如堕梦幻,直到它们完全失去踪影,我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抬头看父亲,试图表达一下自己的感受,但突然失语,觉得无以言喻。它们如此高大神俊,远远超乎我平素的想象,寻常之马与它们相比,简直可以说就不是同一物种。尤其是那匹棕黑毛色的领头马,长宽高都更胜其余,筋腱突露,蜂腰修腿,整个体态精简如几何形;左胸、右腿,各有一处巴掌大的血痂,尘土遍身,扬头缓行,从距我不到十步远处施施然而去,那情形,事后想来,真有点“王者百战归”的味道。
那之后,我就迷上了马,迷到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每晚躺在床上,就专心致志地想马,想各种毛色的马,觉得是莫大的享受;但无论是哪种毛色的马,其原型,都还是那匹在一中操场上看到的领头马:同样高大精瘦,同样在胸前腿上有巴掌大的血痂,还有遍身的尘土——在我看来,那正是战马的标志。我每每想象自己骑着这样一匹大马,飞渡关山,冲锋陷阵……直至神志困乏,渐入梦乡;而睡着之后,常还能接着睡前的情节,继续梦见马。只是睡前的想象可以随心所欲,睡着之后却由不得自己。某次我梦见自己进入一个操场,里面全是高头大马,任人选骑,但每一匹都高到几乎入云,根本没法骑上去,我只能在那些桅杆一样的马腿间徒劳地转来转去,心情遗憾之极、沮丧之极、焦虑之极,以至像受了惊吓一样猛然醒转过来。成年之后,无意间看到西班牙超现实主义画家达利的名作《圣安东尼的诱惑》,不禁十分惊讶:如果画中没有那两头大象似的怪物,而马的数量再多一些,简直就是我的梦境毫发不差的写照。读高中时,父亲给我看过一本他平生最喜欢的小书,美国亚美尼亚裔作家萨洛扬的《我叫阿剌木》,其中第一篇《漂亮的白马》,起首就有这样一个情节:某个夏天的早上,九岁的阿剌木被堂兄叫醒,“我跳下床,朝窗户外边一看。我简直信不过我的一双眼睛……我的堂兄摩剌德骑在一匹漂亮的白马背上……”看到这个段落,我恍惚觉得这也是我曾梦到过的一个情景,尤其是那种突兀而令人惊喜不置的氛围。
八九岁时,开始随父亲的好友、画家杨国勋杨伯伯学国画,先是青蛙、大雁、公鸡,继而是马。也许是因为太过喜欢马,观察既仔细,画得也比别的用心,所以没画多久就得到杨伯伯的表扬。我很得意,写信给重庆的二舅,大言炎炎,扬言决不受徐悲鸿的影响,具体措施是:他写实的地方我写意,他写意的地方我写实。以为如此就和他划清了界限。多年后二舅都还记得此事,曾当作笑话说给父母听。那几年我画马画得上了瘾:宣纸上、毛边纸上、报纸上、蒙了灰尘的玻璃上、学校的黑板上,走廊的墙壁上、作业本上、课本上……哪里都在画。记得有个同学过生日,我用铅笔在作业本上画了一百零八匹姿态各异的马作为礼物送他,每匹马都只有指甲壳大小。几天前和表弟邹欣聊到这件事,他还补充了一个细节,说那一百零八匹马中,有几匹我还画了长长的生殖器,差不多跟马腿一样长,问那是什么,我说是马屙尿的东西……
我曾画过的那些马,如今留在手上的只有两张照片,原本有一幅水墨的斗方在重庆,那是某年外公到贵阳来住了数月,回渝时要我画一幅带回去,说要裱好了挂在墙上。外婆病危时,我和母亲去重庆,发现果然挂在外公的客厅里,只是装裱质量极差,已经干缩起皱,还蒙上不少灰尘,让我暗自不高兴了好一阵。几年前外公过世,和外公同住的三舅新近又搬了家,那幅马就不知落到什么地方去了。前几天突然想起这事,就让母亲和三舅通电话时记得问问:如还在,他们又不喜欢了的话,就请寄还给我,算是留个童年的纪念吧。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有人在贵阳小关附近开设了一个军事俱乐部,占地面积很大,各种轻重武器一应俱全,甚至还有一辆货真价实的坦克……但这些对我来说吸引力不大,让我喜出望外的是其中居然有个马场,而且承包马场的恰好是我的一个朋友。据他说,马场的全部六匹马均购自云南的骑兵部队,也就是说,全是真正的军马,就连驯养员也都是些退伍的骑兵。那段时间,我算是过足了骑马的瘾。也许我与马真是有些缘分的,骑上去就能狂奔,以至我很瞧不起那些由驯养员牵着辔头缓步而行,却还在马背上战战兢兢大喊“慢些”的人。记得其中有一匹两岁半的蒙古马,身架较其余略小,却是速度最快的,我曾骑着它与那些驯养员比赛,跑了第一,得意之余,四处炫耀,末了,还总不忘记强调一句:那些驯养员可都是些真正的骑兵呐(我至今困惑,到底是他们让着我,还是我真是骑术超群?)有一年省作协请了一些著名作家到贵阳开笔会(我记得的有苏童、叶兆言和方方),日程之一就是到军事俱乐部游玩;来到马场,他们都踌躇起来,那些马看上去确实是太高大了,成年人的头顶不过才及它们的背脊,需要蹬两级木梯,上一个高台,这才能顺利跨上马背。我在一旁看他们相互客套推让,不禁技痒难忍,一声不吭上了其中一匹,奔驰一圈回来,下了马,正喘气,苏童踱过来,问我,这马应该怎么骑呀?于是我就给他说腿该如何如何,腰又该如何如何……苏童是我喜欢的作家,而我曾教过他骑马,这在我的生活中算得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只不知他最后学会没有?还记不记得这件事?记得了会不会承认?
军事俱乐部的生意红火了几年,渐渐似乎就清冷下来,去的人越来越少,等到承包马场的朋友离开后,我也就不再去了,只听说那些军马一匹一匹相继死去,令我心痛不已。再后来,几乎就不怎么听得到军事俱乐部的消息。前两年坐车去金阳新区,半道上看到路边杂草丛里赫然蹲着一辆锈迹斑斑的坦克,这才想起,那正是当年军事俱乐部所在的地方。
没地方再骑马,要想过瘾,就只能是偶尔到花溪的乡间去骑那些当地农民喂养的土马,但你看它已然十分地努力用劲了,却还是跑不快,真让人不得不有沧海巫山之慨。我如今对马的喜爱,全都寄托在欣赏那些有关骑兵的电影上,比如《拿破仑在奥斯特里茨》、《勇敢的米哈依》、《斯特凡大公》、《铁骑雄狮》、《勇敢的心》、《影子武士》、《第一骑兵军》、《魔戒三部曲》、《亚历山大》等等,每隔一段时间,我总会找出来,专挑那些骑兵冲锋的段落看。印象最深的是《勇敢的心》中英格兰重骑兵向苏格兰起义军冲锋的场面,以及《铁骑雄狮》中澳洲轻骑兵向土耳其阵地冲锋的场面,前者骑兵的数量并不多,却拍出一种肃杀阴沉的气势,令人胆寒;而后者壮观之极,演员个个骑术精绝,其迅猛有如雷霆闪电,每次都看得我揪心攥拳,呼吸急促。不过最感人至深的还得算《第一骑兵军》中那最后的情景:战役结束,集结号响起,许多骑士已经战死,而战马们仍驮着空鞍,纷纷从硝烟中奔驰而来,回到自己的位置……
苏联作家巴别尔的《马背日记》,市面上曾卖过好几个版本,其中一个载有大量图片,有一帧是某个红军军官骑在马背上,举着望远镜察看远方。他胯下的坐骑,是我平生仅见(无论是书上、电影里,还是生活中),唯一能与我当年看到的那匹领头马相媲美的一匹。那匹领头马当然早就死了,它不会知道有个人几十年过去,都还记得它。
 帕布莉卡
帕布莉卡

 爱是一颗心遇到另一颗心(出处+配图)
爱是一颗心遇到另一颗心(出处+配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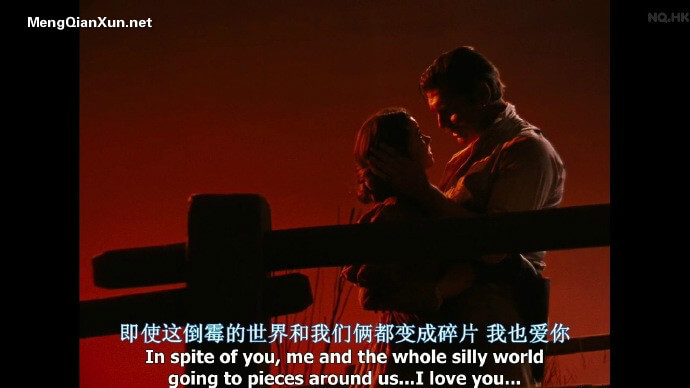 《乱世佳人》电影专题
《乱世佳人》电影专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