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关何处
张毅,在《当代》《小说选刊》《小说月报》《散文.海外版》《散文》《红岩》《散文百家》等刊物发表小说、散文多篇。散文入选多种选本。
文化学者爱德华.萨依德写文化身份情境《乡关何处》一文时说,要记载一个被遗忘的世界,一部属于离乡背井、变动不居的身份认同的回忆。“乡关何处”的迷惘,可以说是20世纪文化情境下,解析人类自我迷失的一把钥匙。对离开故乡的人而言,则存在一个被城市认可、融入和接受的过程。
你是哪里人?你老家在哪里?在这座移民城市,“老家”是一个被反复追问的话题。
高密是我的出生地,祖辈在那块生长高粱的土地上繁衍生息,人丁兴旺。来青岛前父亲阴着脸说:上那地方干什么?人生地不熟的。听到这话如同有堵墙立在我和父亲之间。那时,从老家高密到青岛,中间有十几个车站。我最早坐“火车”是从一个小站上车,那个车站叫姚戈庄站,是胶济线一个四等小站,建于德占胶澳初期。现在这个小站已经废弃。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一天,两条钢轨在阳光下延伸着,信号灯像老人昏黄的眼。一辆火车缓缓驶来,车门打开了,我是被父亲推进车厢的。那时,高密到青岛90公里的路程,火车要运行四个小时,早晨出发,中午到达。
我最早住在青岛一条老街上。老街路面是石条铺的,周边散落着上世纪初的德式和日式建筑,铁路与港口在附近交汇,货轮汽笛和火车的尖叫声此起彼伏。租界时,老街有很多卖丝绸、烟土和洋火的老子号店铺。解放后,政府把店铺拆了,盖了几排二层楼,灰砖红瓦。因为潮湿,门前长满了青苔,房门响起的时候,浑浊的吱嘎声在街上回荡。雨天时,雨水沿着瓦缝往下淌。晴天时,家家户户在窗口横根竹杆,人们把衣服从箱子里搬出来,在太阳下晒。老街到处是海藻和臭鱼烂虾发出的气味,还有房间角落里的潮湿霉味。这些复杂味道只有大风才会把它吹走,换上一些新鲜空气。
老街居民大都是岛城开埠以来的移民,虽非土著,大约也在青岛生活了近百年。我们二楼住着六户人家,邻居共用一个厕所和水池。经常天不亮就被各种声音弄醒,开门的声音、做饭的声音、咳嗽的声音、下楼的声音……外面黑乎乎的,看看闹钟,差十分六点,那是王姓邻居去赶电车了。他是一个火车司机,每天赶5路电车去郊区一个小站。早晨洗漱时,人们把水舀到脸盆里,不断传出牙缸和脸盆的碰撞声。走廊墙壁斑驳脱落,每家门口都有个砖砌的煤池子、几双旧鞋、一辆旧自行车和过冬食用的大白菜。楼顶常有一只猫,绿幽幽的眼睛像在下雪,它在逮老鼠。猫在墙头、路边以及灯光暗淡的角落里不断跳跃着,它总是对我视而不见……
窗外,一辆有轨电车开过来,慢慢在街头停下,很多乘客下了车,电车慢慢开走了;夕阳西下,海面飘来一艘木船,妇女们急匆匆朝码头走去,海风吹拂着她们。她们手搭凉棚遮挡正在下落的太阳。海边的小码头上,几根腐朽的木桩立在那里,旁边有几条陈旧的木船,木船被一根乌黑的粗麻绳拴着,在水面上晃晃悠悠,仿佛是被风摇动的一片叶子。人们把船拖上岸,系住缆绳,收好帆和桨。鱼在网里跳动,人们背起鱼网朝岸上走去。石子路斜坡向上,通往老旧的楼梯或幽暗的木门。
我住的这栋楼没有门牌号,因为条件太差,朋友问起住处时,我总是语焉不详。我说,啊,那地方就是一个胡同,进了胡同往左拐,再往右拐……我住的房间阴暗潮湿,白天见不到阳光,蟑螂是这里的常客。白天,蟑螂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夜里一开灯,就可以看到地上、桌上大大小小的蟑螂四处乱蹿。碗碟每天吃饭前都要冲洗一遍,因为碗碟上经常有蟑螂的痕迹。一个夜里,儿子突然被什么惊醒,他在床上大声叫喊。我赶紧起来开灯,发现枕头上有几只蟑螂,正瞪着眼睛和我对峙。我举起苍蝇拍,蟑螂迅速跑到枕头下面,我翻开枕头,蟑螂又跑到床下。我拿起手电筒,翻身跳到床下,蟑螂继续用挑衅的眼睛看着我。我用苍蝇拍扑打过去,蟑螂却消失了。我翻开家具、纸箱、暖水壶,发现目光所到之处,都有蟑螂用挑衅的眼睛看着我。我和蟑螂的斗争直到搬离老街才结束。
某个冬夜,我在家看塔可夫斯基的电影《乡愁》。这是一部讲述俄罗斯民族精神的电影。《乡愁》叙述了一位俄国教授——戈尔恰可夫在意大利与美丽的女翻译——多梅尼科间微妙的关系,以及置身异国他乡时的记忆和梦幻心理。戈尔恰可夫对多梅尼科的访问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造访,是两个民族心灵的对话,其意义不亚于人类访问火星。多梅尼科的死则使戈尔恰可夫失去了对生命的尊敬,他决定回俄国,不久便悬梁自尽。影片中,我更注意多梅尼科和狗的一组镜头:人与动物息息相关却又爱莫能助,最后是多梅尼科渐弱的眼神。《乡愁》里有一组关于“家”的片断:草坡上的房屋在烟雾中时隐时现,远处有几棵树、两匹马、一只狗以及乡亲忧伤的身影。画面透着对家园深切怀念和永远无法回归的情愫。在这里,塔可夫斯基要说的不是具体的“家,”而是关于人类深层意义的心灵史。
电影的乡愁气息深深影响着我。“乡愁”对于我是一种不折不扣的思念,它常在某个时刻悄然来袭:月圆时分或当夕阳西下,一片落叶打在自己肩上……老家是一个安静的乡村,一条河响在记忆深处……童年总是被一场大雪笼罩着。雪落在肃穆的树枝上,落在高高堆起的草垛上,落在故乡开阔的平原上。北风从村后的高坡鱼贯而来,发出“呜呜”的鸣叫,河流冰冻的声音从地表传来。读高中时,我每天迎着寒风,用棉帽蒙住脸,步行10里去县城求学。雪野里,我像一片雪花随风飘荡。冬天过去,暖风频吹,屋顶的积雪开始融化。屋檐下,一串串钟乳石一样的冰凌在暖风吹拂下,发出隐隐的爆裂声。能够看出冰凌日渐缩短,冰水从冰凌尖上落下,在地上溅出一个个小土窝。夜里偶尔传来冰凌的坠落声,让人梦里多了几分凉意。白天的时候,我看见有一串冰凌在屋檐下摇摇欲坠,好像不会坠落,就在我转身之际,身后突然响起一阵破碎声。我在那个村子看见生命中第一场雨和雪,听到亲人的声音在耳边响起,知道了黑夜与白昼的关系,懂得了四季轮回的规律。现在,那个村庄已被一片厂房覆盖。
我有个邻居叫阿芳,她的家在重庆巫山一个小镇上。她来青岛前,家乡的小镇已经被水淹没。巫山我去过,那是我和老三峡的告别之旅。我们坐的是宜昌去奉节的渡轮。那艘渡轮有些旧了,船体锈迹斑驳。渡轮在江里行驶一段时间后,在一个渡口停下。导游告诉我们,这个县城叫巫山县,今晚我们就住在这里。然后她指着老城的房子说,你们看到的是最后的巫山,这里明年就要被水淹了。果然,三峡大坝截流后,巫山老城被淹没在水下50米深处……阿芳有个五岁的儿子,男孩眼睛很大,一脸忧郁。阿芳不在时,男孩常在街上张望,几个打工者每次走到这里,都爱逗他玩。他们说,小孩,把你的小鸡鸡露出来让你爹看看。男孩就劈开腿,把小鸡鸡露出来。
打工者嘻嘻哈哈笑着说,小孩,叫爸爸。叫我爸爸。
男孩扭头说,你不是我爸爸。一会儿我爸爸来揍你。
我爸爸一会儿就回来了。打工者听完笑着说,
你爸爸?连你妈都说不清你爸爸是谁。哈哈……
傍晚,阿芳去上夜班了,留下男孩自己在屋里。路边店门早已关闭,淡淡的灯光随着地势上升,静静地悬在远处。有几次我半夜去厕所小解,迷迷糊糊看见阿芳从楼下走来,身后跟着一个陌生男人。时间长了,我知道,阿芳是发廊的按摩女。阿芳有个男朋友,也是三峡库区人。他们是在打工时认识的,两人同居后,阿芳怀孕了,后来生了孩子。他们经常为了生活争吵,因为钱总是不够花。为了把孩子养大,男朋友去一个煤矿挖煤。有一天男朋友回来说,要和另一个朋友去外地贩水果,大概半年时间。阿芳说你就去吧,只要能多挣些钱回来。男朋友去后一直没回来,阿芳一打听,男朋友在外面又有了一个女人。
夏天的傍晚,老街路边摆了许多桌子,空气中弥漫着馄饨和烤鱿鱼的味道。很多游客在这里买几串烤鱿鱼,喝几杯啤酒,然后依在栏杆上看海。小伙子们粗鲁地笑着,姑娘们在窃窃私语,人们都在这里找到自己的乐趣。我有一次路过阿芳的发廊,看见她正在给一个年轻人做按摩。那天,她穿一件粉色的紧身内衣,露出深深的乳沟。年轻人的头挨近阿芳胸前,她的十指在年轻人头上、面部、脖子上起伏着,她的胸总是有意无意地碰着年轻人的头。年轻人闭着眼,显出一副陶醉的表情。那一刻,阿芳仿佛在年轻人身上用了巫术。收音机传出一首流行歌曲:雪在烧……雪在烧……风中的花朵……绝望地奔跑……年轻人做完按摩刚走出门,进来一个中年男人。男人和阿芳私语了一会儿,便随着她去了里间……半小时后,阿芳和中年男人走出来,男人把钱塞到阿芳领口,顺手摸了一下她的胸,转身往门口走去。阿芳说了一声,再来呃,刘老板。回过头来低声骂了一句,臭男人……晚上十二点后,卖馄饨和烧烤的商贩撤了摊位,老街立马清冷下来。发廊里传来“雪在烧,风中的花朵,绝望地奔跑……”歌手嘶哑的声音在货轮汽笛声中忽隐忽现。
我另一个邻居姓刘,80多岁,是最早的岛城移民,住在不足8平米的陋室里。他年轻时在码头做苦力,现在老了。问他老家是哪里的?他说记不得了。刘大爷是个修鞋匠,每天坐在老街路口,戴一付老花眼镜,反复用锤子砸一双鞋。他偶尔会抬起头来朝远处看看,然后点一支烟。烟是“葵花牌”的,两毛钱一包。抽到半截,用手掐灭,放在工具盒上,等下次再抽。刘大爷每天自己生炉子做饭,烟薰得一把鼻涕一把泪。夜里,他咳嗽的声音像是楼顶掉下来一块砖头,老远都听得见。我有时担心他一口气接不上来,就背过去了。有段时间,很久没看见刘大爷出来修鞋。那年除夕,街上已是焰火满天,老人早早把门关上了,他已习惯了孤独。我在门外敲了半个小时,只想送上一句问候,他开门后满脸泪水。正月十五晚上,刘大爷在隔壁喊一个人的名字。从那天开始,他晚上都在喊那个人的名字,像在哀求,又像是呼救。隔几分钟就喊一次,他的声音随着时间渐渐微弱下来。没过多久,刘大爷死了。那天下过一场雪,气温陡降了许多,天气阴冷。我到他屋里时,看见几个邻居都来了,连平时和他不讲话的吴老头也来了。人们脸色沉默着,为一个老人送终。刘大爷被邻居们抬着,一步步走出老街。街口停着一辆小型卡车,载着他去了位于郊区的火葬场。
事后,有人说他其实不姓刘,只是没人知道他到底姓什么。
他是谁?他的老家在哪里?他有儿子或女儿吗?
他和每个老街的邻居一样,经历了生命所有的快乐和悲伤。有平静的、喑哑的,还有我们不知道的人生秘密,然而现在一切都结束了。
我在青岛住过很多地方,印象最深的是八号码头,我把那里称作“北海道。”那些年,八号码头业务繁忙,海面常泊着装满集装箱的货轮,货轮钢柱上挂着五颜六色的旗帜。来自各国的船员常从高高的眩梯上走下,沿海边的水泥路走出港务局。那里有一条铁路专运线,是为进出港货物运输修筑的,同时还修建了一些铁路工房。我住的工房位于八号码头北面,那里位置偏僻,周围杂草丛生,除去正在作业的港区工人外,偶尔会有拾荒者流落至此。夜里,除去港区孤零零的灯光外,周围一片黑暗。有夜航飞机从天空掠过,两朵翼灯星星一样忽闪着,虚幻而飘逸。几根强烈的光柱交叉着从夜空扫过,那是军港值班官兵在巡视海空。一阵汽笛从海面传来,那是一艘正在靠港的货轮。夏天,会看见戴草帽的钓鱼人在岸边竖几支鱼竿,气定神闲的等鱼上钩。到了冬天,北风裹着胶洲湾的寒气迎面扑来,冷风刺骨,大风刮得人左右摇晃。那时,我每天骑着自行车,带着儿子穿过港区的水泥路,把儿子送到学校,再去位于前海的单位上班。码头散落着许多大型起重设备,货场堆满海外运来的红色矿石和大堆煤炭,阵风吹来,煤灰和矿石粉末满天飞舞。水泥路上常有一层黑糊糊的煤灰,或是红色的矿石粉末。每次从水泥路上经过,我都努力加快速度,让自行车迅速穿过空中弥漫的灰尘。
离开8号码头前,我独自一人在岸边观望落日。那是个秋天的傍晚,风呼呼吹着,我看见水泥路上有一个人影。那个影子越来越大,我终于看清了,那是一个年轻人,正骑着自行车走在我经过的路上,身后是一个正在上学的孩子。因为风大,自行车被吹得歪歪扭扭,他躬着身体使劲儿往前推着。风像考验我一样,正在考验着这个年轻的父亲。我的经历,正在被这个年轻父亲复制着。
这座城市有说不尽的恩怨情仇,它已被岁月诉说并将继续诉说着。这里的每座建筑、雕花的铁门、粗砺的石头;夏天灼热的阳光与涛声穿过玻璃;时而平静时而狂暴的大海;沙滩裸露的皮肤与被海水浸透的木船;电车划过夜空时尖锐的呼啸和窗外起伏的叫卖声……它们像时间的沙砾从我手指间滑落,在落日的余晖里。来自故乡平原上的风携着庄稼的气息与海风不断吹拂着我,只是故乡的风已渐渐成为一股弱气流,而海风以入侵的姿态更加有力地吹拂着我。来岛城多年,我已融入这座城市。我的衣着、表情和习惯完全和青岛土著无异,我的口音已蜕去了乡音的土腥味。
我经常做同一个梦:我越过几个车站和商店,希望找到路边那个邮筒。我想给记忆中的故乡发一封信,人们告诉我,那个村庄已经消失。是的,如今,故乡只有梦中才能见到。随着时间流逝,故乡就像一张年画,在微光中渐行渐远。
原发2020年7期《散文百家》。
 帕布莉卡
帕布莉卡
 李兰迪 写真集
李兰迪 写真集 小彩旗 写真集
小彩旗 写真集
 爱是一颗心遇到另一颗心(出处+配图)
爱是一颗心遇到另一颗心(出处+配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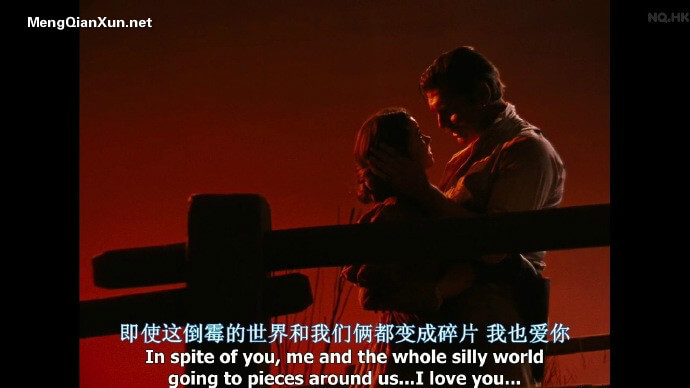 《乱世佳人》电影专题
《乱世佳人》电影专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