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城的文集出新版了,不方便买,就写一篇文章给阿城老师做个不要钱的小广告——当然他这个身份也不需要我造势就是了。
叫他一句老师,是说我也对他的那种力道有所向往,但渴望是渴望,我和他,总归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的。阿城的那些东西我一辈子也写不来,不只是因为经历不同,而是因为他对中文文字的拿捏实在太好了,他和所有的那些写文革、写改造的作家都不一样,别人是写伤痛(当然的确也都写得好,看得人潸然泪下),而阿城是写过日子,有滋有味的日子,可看上去快乐,心底是苦的。别人的文章看完了你咬着牙说文革真是万恶、说下乡改造改烂了多少人的命,而阿城,你看了他写的每一个字,最后只能叹气说一句“唉,那就新中国万岁吧”。
现在看阿城的人逐渐少了,对写作有神往的年轻人,多是喜欢追捧王小波。“王小波写东西有时会飞起来,用人的想象力去脱离人世的苦,而阿城是走进这苦难里去”。大家一谈阿城,总是喜欢拿他和别人比。汪曾祺、王朔、贾平凹、莫言……都拿来比了一通。可阿城就是他自己。
▲阿城
要说他神在什么地方,便是在半页纸上就能给你写出一条鲜活的生命了。他写王一生吃饭,看了以后不觉得他在吃饭,而是觉得他在吸什么天地精气日月血肉,滴滴不舍得落下似的要吞个一干二净;看《孩子王》的王氏父子砍树,砍的也好像是虬结苦痛的穷人命运了,他们挥斧子带起的风,若是天上真有什么战神在盯着看,也准得叫这人类的肌肉扭动和手起刀落的模样给吓个瞠目结舌;就连他写树也是独具一格的,巨树立在林中是活生生的,被砍倒了,那一阵轰鸣震得人上下牙都敲在了一起。他的这“三王”,颇有种虚虚实实、摸不清远近的感觉,你分明知道他在写自己的故事和真实经历,可他偏偏就是能将这一切写出局外人的感觉。仿佛每一个传奇的故事他都飘在半空,不带感情地观看了全程。那故事你从未也绝不可能亲历,但它们活生生地在你眼前划过。
而当他换一支笔写起散文和随笔时,他也像换了个灵魂,忽然之间离你很近。他能开出中国中年男人特有的玩笑,可又不显得低俗,只是言简意赅,只是可爱(”我本来正要去厕所,此时急用锁阳收阴功,枪子儿不长眼,轻起即妄动,犯不上为了肚子里的一点废水,把命搭上”)。他用平实的言语为你讲故事、同你谈天,可你听他严谨柔和的措辞,又能明白这不是个仅仅只是来聊天的人。他像是希望你能从他的故事里看到点什么、学到点什么,可你到最终是否真的能明白什么,他却又无所谓了。这时尘归尘土归土,故事的就让它回归故事。
这就是为什么大家总说阿城是最会讲故事的人。
窦文涛曾是阿城的学生,他在谈起阿城的时候,说他是最会聊天的人,导演贾樟柯也说过这句话,“他实在太会聊天了。”这样的话他反反复复说了很多遍。嘴贱得无人能及的马家辉在聊到阿城的时候,也不禁有点畏怯甚至是灰溜溜的意味——他当年在香港当场调侃了贾樟柯几句,谁知阿城转眼在台上便公然批他“可见文化和学问是不成正比的”,牙尖齿利的马家辉都有些愕然了:“你,你不能这么在公众场合批评我嘛。”即便如此,他也未曾对此有过怨言,只是苦笑着说阿城这样还是很坦诚,毕竟是替朋友出头、蛮有气魄的。大家都爱阿城,没人会恨他,因为当今世上能够说得上是“有意思的人”太少了。一身的才气,什么他都能聊,温和有趣,而且会生活,大家津津乐道的一件事便是他家里穷得叮当响却买了好几万块钱的音响。
别人写字是为了生活,而他要先愉快地活着,再写字。因此他这个有话直说的习惯也算是贯穿了始终,他讲到自己写《闲话闲说》,指名道姓评论了不少人,比如贾平凹,比如莫言,这实际上是很犯忌讳的。一般人可能要自责一下自己的失言,以后在人前要更加慎言慎行。可阿城面对众人时,提到这个问题便会直言“我对贾平凹先生很尊敬,但提问里具体回答,就针对该问题,但不够全面。回到国内时候,他们就说你不可以这么想,要绕点弯子,直接说的话销售会受影响。所以以后这个问题我不太回答。”简单来说就是:我写的时候没想那么多,你们也别曲解,其实我还想就事论事,但是这样讲话影响销量,所以以后这种问题我不回答。——很直白,可又让谁都生不起气来。从而这样的直白就变成了一种可爱。王朔说北京那种侃爷已经不多见了,饭桌上一个人引导话题,众人听着他天南海北地说,阿城就是这么一个人。他是作家——虽然他自己不愿意这么叫自己,他说人要写了足够多的东西才能称之为什么家——但他比起一个文学家,更该说是个文化家。他什么学问都有,只要你能问的出,他就能回答的上,民俗学、图腾、禅宗。侯孝贤更是请了他来做聂隐娘的编剧,因为他“对唐代太熟悉了,用的碗、喝水的杯子,他都知道应该是什么样的”,每一件器物就是一段器物史,而这正是阿城所痴迷所擅长的。当年他那位做电影评论的文化人父亲曾惦棐被打成右派,他不能去接受毛主席接见,只好每天流连于家附近的琉璃厂,研究文玩,这些都是他的机遇。
▲《棋王 树王 孩子王》
作者:阿城
因而从“三王”中所看到的知识分子形象比较与众不同,那些都是他的影子,可又不全是。《棋王》中的“我”所说的一些话实际上更体现了阿城本人的哲学理念,里面有一个情节,是王一生不理解“我”为什么总要追求看个电影看个书的心情,“我”心中隐隐觉得这种渴望是不能放弃的,但是又说不清到底是为什么,总觉得是和活着有关的东西。这是那时候下乡改造的知识分子一种普遍现象,世道苦,就只能投身到别的上面,譬如“艺”的升华。像王一生下完棋哇一声哭出来一般,这里面有精力竭尽的宣泄,也有生活中的痛苦,是悲惨和超脱融为一体的形象。阿城自己就是这种文人,他“和主流保持距离”,过自己的生活,不止能写人的灵魂在黑暗大门之后的焦灼,更能写出一种生活的东西,这是我们这一代、上一代,甚至下一代,都写不出来的。鲁迅当年说废名“不够广远”,我这一代所看到的这个时代的作家,何止不够广远,都仿佛油花浮在凉水上一样。而中国,尤其是当下这个浮躁、阶级极度割裂的中国,尤其需要能写沉重东西的人。——也需要敢于写沉重东西的人。
对于上一代人,他们和阿城之间的记忆远比我这一代人多,他们眼见他高楼起、宴宾客,听着他在美国自己组装老爷车的故事长大,看他抽那只小烟斗,阿城是作为一个传奇的人出现在他们生命里的。到了我这时,总感觉太晚,他从一个传奇的人,变成了一个传奇,说远也不远,但也绝对不近。然而不管怎么说,阿城这样一个人,他的出现对于所有人来说就是一个奇迹,哪怕他不再写书,只要知道和他活在同一个世界中,对于文化、对于整个民族来说,就不是太糟。
他这高楼起来,千百年都不会塌下去。
编辑:殊白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帕布莉卡 » 《棋王》观后感 :阿城之于我,之于所有人
 帕布莉卡
帕布莉卡


 爱是一颗心遇到另一颗心(出处+配图)
爱是一颗心遇到另一颗心(出处+配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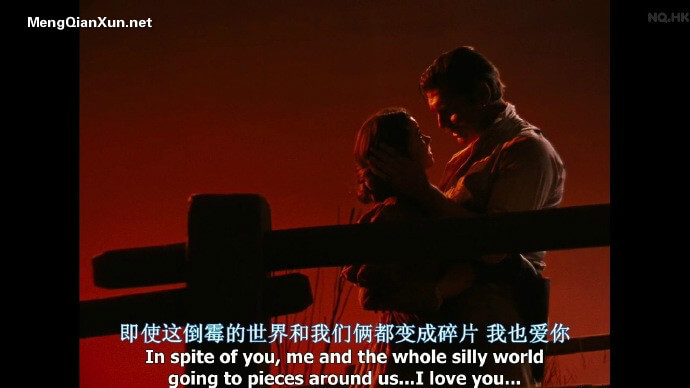 《乱世佳人》电影专题
《乱世佳人》电影专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