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更斯(Dickens)对于《大卫•科波菲尔》有一段著名的表述:“在我所有的作品中,我最喜欢这一部。”原因显而易见:主人公童年在工厂做工和饥寒交迫的残酷经历就是狄更斯童年的写照。不仅如此,作者在他挚爱的姐姐受尽病痛折磨终于死去后开始写作,这段经历也为小说中的关键场景提供了创作灵感:科波菲尔挚爱的朵拉长期患病、因病而死。(一读到这个场景我就禁不住落泪,再没有其他原因能让我这么快就泪眼滂沱。)
第一次阅读《大卫•科波菲尔》时,我才十几岁,在康涅狄格州韦斯特波特与奶奶一起度过夏天。我很喜欢奶奶,不过她并不是个随和的人,而且她白天大部分时间都躺在“拉兹男孩”休闲椅上,喝着白葡萄酒看高尔夫比赛。于是,我就坐在户外阅读。刚看到书的开头几句,我就被深深吸引了。“我是否能成为我自己生活中的英雄,还是会有别人来扮演这个角色,这本书会告诉你。”我和奶奶在一起单独待了几个星期。阅读这部神奇的书时,我和大卫、艾米丽(也叫小爱丽)还有朵拉成了朋友。

当然还有斯提弗斯,这个年长一些且极富魅力的上学的男孩,把小大卫当成小兄弟。狄更斯将他描述为“英俊的男孩”,大卫•科波菲尔完全被他迷倒了。我也一样。斯提弗斯第一次出现的章节以大卫注视着熟睡的他结束。斯提弗斯给大卫的人生和运气都带来了转折。尽管后来他有点无赖(尤其是对艾米丽的态度),不过如果没有他就不会有大卫•科波菲尔——他拯救了大卫。因此当我回忆起这本书时,几乎想不起来斯提弗斯的卑鄙和背叛。相反,我能记起他收留了大卫,当大卫最需要他时两个人之间的心灵交互。我原谅了他,就像大卫原谅他一样。
在那个很久以前的夏天,当我合上书时哭得比读到朵拉去世还伤心——因为我已经开始想念书中的人物了。
当我写关于我母亲和她离世的书时,有些朋友问我是否希望以此来做个“了结”。我知道自己并不想要结束,而是想继续我们的对话。一个人离开世间并不意味着他们离开了你的生活。我清楚地记得那个读完《大卫•科波菲尔》的炎热夏日。但是我与大卫、艾米丽、斯提弗斯和朵拉的交流并没有结束——而是刚刚开始。我与他们对话并与他们共存,就像我现在依然与母亲对话那样。
对于《大卫•科波菲尔》中的人物,我并没有像想象中的那么怀念他们——因为我从不需要和他们说再见。这些角色不会离开我,我也不会离开他们。《大卫•科波菲尔》直到今天还陪伴着我:大卫•科波菲尔这个角色,以及他折射到生活中的那些我所认识的大卫。
大卫们在我的生活中发挥着不可思议的作用。诚然,大约五十年前大卫是个很流行的名字,可以排在第二位。我小学所在的班级里有四个大卫。我是唯一的威尔(Will)。直到现在我也不愿意用人口学或是偶然事件来解释这一现象。
我交到的第一个最好的朋友名字就叫大卫。我们在幼儿园认识,上学的时候形影不离,连续好几年的周六都轮流去对方家里过夜,一起去夏令营,并且一直保持密切联系。他和他的妻子邀请我做他们其中一个孩子的教父,并以我的名字给另一个孩子取名。尽管我们分别住在美国东、西海岸,但是每当有重要的事情发生,我都会在第一时间通知他们。
我写了一本书,收录了与一位名叫大卫的朋友的往来邮件。
我丈夫也叫大卫。
还有大卫•拜耳。我是在1980年9月刚上大学后不久和他相识的。我们住在相邻的套房。虽然我也很喜欢我的室友,但是却没能和他们建立深厚的感情。至少在我看来,我和他们不太协调。大卫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于是我们发现了彼此。
现在,通过不停地拍照片、更新博客,让我们能够在多年之后通过这些记录找到第一次遇到生命中最重要的人,那些改变了我们生活的人的时刻。在我以前的那几代人都更擅长写日记,正因如此,过去的几百年里人们将自己的印象通过打印机记录下来。不过我的记忆已经模糊了。我并不能确定遇见大卫•拜耳的那一天。
不过我还清楚地记得,开学后的一天,校长向新生讲话时提到我们当中有一名学生只有十六岁。因此,当我第一次见到大卫时,我确信他就是那个十六岁的学生。他比我矮几英寸(几厘米),那么他肯定不够五英尺五英寸(1.65米)。他身材纤细结实,有着橄榄色的肌肤和杂乱的黑头发,他的下巴棱角分明,思考的时候撇向一边。我不知道当时是否直接问过他,不过后来我发现他其实和我同龄。我一直也没有发现那个十六岁就上大学的人是谁。
最开始我们彼此很友好,接着我们做了朋友,后来做了最好的朋友,最后还做了室友[和来自新泽西州拉姆森的天生好脾气的鼓手住在一套公寓里。我们管那个鼓手叫梆梆,既因为他敲鼓,也因为他高昂的热情让我们想起了《摩登原始人》(The Flintstones)里派博(Pebble)的老伙计]。大卫看上去像极了来自东海岸的人:皮肤黝黑、信仰犹太教、有点愤世嫉俗还很热情。但是他其实来自洛杉矶,一个在圣莫妮卡北部的叫作乡村峡谷(Rustic Canyon)的地方,对,就是这个地名。

《摩登原始人之摔跤赛攻击波》
不久之后我见到了大卫的父母。他的妈妈是一位学校校长,父亲是一位在兰德公司工作的物理学家。最后我见到了他的双胞胎兄弟。在我看来,他们只是长得有点相像,而其他人却分辨不出他们。在他们众多的差异之中,有一项对于那个年纪的我们尤为重要:大卫是同性恋而他的兄弟不是。
大卫和我喜欢的东西简直一模一样,不过我们喜欢的理由却不尽相同。正因如此,我们一旦聊起来就没有止境。我们一致认为辛迪•劳帕(Cyndi Lauper)会比麦当娜更出色、更经久不衰。大卫认为劳帕的嗓音让人难以忘怀,而我认为她的歌词更有内涵。我们都喜欢当地一家叫那不勒斯的比萨店,但是大卫喜欢肉桂烤面包,而我总是点面包片。我们都喜欢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Francis Ford Coppola)改编自阿尔贝•加缪的《局外人》的同名电影The Outsiders,大卫喜欢帕特里克•斯威兹(Patrick Swayze),我则喜欢马特•狄龙(Matt Dillon)。

电影《单身男子》壁纸
我们对书籍的态度也是如此。我们都为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的作品疯狂。但是大卫最喜欢的是小说《单身男子》(A Single Man),而我则为他的回忆录《克里斯托弗和他的同类》(Christopher and His Kind)着迷。大卫•拜耳也喜欢《大卫•科波菲尔》,和我一样,他喜欢这本书的初始原因是斯提弗斯和年轻的主人公之间的友谊。不过他认为朵拉之死被过度描写,而我却一直为这个场景心如刀割。正如我说的,他有着愤世嫉俗的一面。要去接受一个用批判的眼光看待世界的人对任何人都并非易事。大卫并不像我那样爱着朵拉。他认为她愚蠢得不可救药,而且她对她丈夫的爱有点让人厌烦。不过我们对待艾米丽的态度十分一致,我们都毫无保留地疯狂地爱她。
毕业之后,我搬到了香港。(我一时兴起,申请了去那里学习和教课的奖学金,不过没有成功。我的兴致更高了,决定自费去那里并成为一名记者。我做了几个月的临时秘书,攒够了买单程票的钱。)大卫•拜耳去了纽约找他的男朋友,并为一名建筑师工作,他攒钱想要去建筑学校,拯救所爱的城市。那时还没有互联网,我们通信并给对方寄明信片。不过大卫在纽约经历的事情太多了,长信都无法把它们说清楚。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他开始用油布的边角在一些区域拼凑“小地毯”。随着这些作品越来越多,它们出现在了报纸的报道上。大卫开始和纽约下东区的作家和画家交往,像涂鸦艺术家那样为城市带来了艺术景观。他答应要来看我,不过要等他攒些钱、等他生活节奏慢一些、等他的申请完成之后。大二结束后的暑假,还有我中途回家更新六个月的香港工作签证时,都和大卫一起快活地旅行。我们承诺彼此,以后找机会还要一起旅行,就选在便宜些的亚洲。
1986年的一天,我身在香港,起床时觉得精神百倍。那是个星期六。我外出完成采访任务,然后回到公寓,想要写点东西。我还记得那最神奇的一刻:前一秒我还感觉不错,实际上,是感觉很好;而下一秒,我就发起了高烧。我感觉自己要呕吐,甚至要晕过去了。我够到体温计,发现自己104华氏度(40摄氏度)。接着我开始冒汗,是那种人们常说的冷汗。我颤抖着,汗水不停从脸上流下来,衣服都湿透了。接着,我就好了,尽管有些虚弱和摇晃。于是我躺下睡着了。几个小时后,我哥哥从纽约打来的电话把我叫醒。电话里,他告诉我,大卫•拜耳在骑车上班的路上撞到了街上的坑洼,自行车失去控制滑向了林肯中心外的一辆巴士,大卫当场丧命。我们一位共同的朋友想要联系我,就找到了我的哥哥。不久之后,我了解到大卫的父亲结束了公差正在飞往纽约的飞机上,在我和哥哥通话后的几个小时后才会降落,那时等待他的是儿子的死讯。
我并不相信心灵感应。但是我发现我无端的高烧和大卫去世的时间吻合。
我从香港飞回纽约参加葬礼。在飞机上我想喝点威士忌。西北航空要收取四美元,而我只有一张二十元的纸币。空乘人员不想找钱。当我看到他们出租耳机——每个两美元——收了很多零钱,再次要求他破钱时,他还是不肯。那是耳机的钱,他不能用来给饮料找零。就在那一刻,我的愤怒差一点爆发。大卫的死让我感到悲痛欲绝。突然,我是这么想念大卫,这思念让我无法承受。我从不知道也从未经历过如此沉重的悲伤和巨大的愤怒,一旦我忍不住开始表述,就将无法停止。
我从一数到十,一次、两次、三次、四次,直到最终睡着。
葬礼上,我和其他人一样浑浑噩噩。我还有时差感。我发现悲伤和时差其实很像——世界以错误的方式转动,你睡不着,即便筋疲力尽也毫无困意,你晕晕沉沉,好像在生病发烧。前一分钟浑身发热,接着马上又觉得冷。最重要的是你觉得很奇怪,没有根基,无家可归。需要有点信心相信这感觉总会过去,恢复原样。人能够很快适应时差,却不能适应悲痛。时差很快就会消失,而悲痛就算能够减轻,在减轻前总要不断加剧。
当大卫•科波菲尔失去了妻子朵拉时,他想到:
这不是我去探究巨大悲痛之下我的精神状态的时候。我逐渐认识到未来没有什么出路,我生命的力量和行动就到此为止了。只有死亡能够为我带来庇护。刚刚遭受痛苦的打击时我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是后来慢慢发现的。
当我失去大卫•拜耳时,一开始我不能相信他真的离开了人世。我一直期望他能再次出现,就像狄更斯小说中的人物那样,在后面的章节里出现。不过随着时间流逝,我终于适应了没有他的世界。这个世界因他的离去而改变,再也不能变回原来的模样。
还有一段时间我十分自责。大卫一直想来香港看我。我为什么不坚持邀请他呢?如果他来了香港,那天他就不会在纽约骑自行车,他可能还活着。我知道这样想不够理性,但是责备自己要比接受飞来横祸容易得多。
在五年时间里一个人能够给人留下什么印象?我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想到这我既感到幸福又感到悲伤。难以忘怀。深不见底。我不能说每天都会想起大卫•拜耳,但是我确实在很多时候都想到他。那些日子通常都是快乐的。想起他的几天后,我意识到自己想到他时并没有明显的失去感。
我喜欢谈论大卫——和我们的朋友,和他的男朋友——我喜欢跟别人谈起大卫。通常这让我高兴,但有时我也会非常想念他。
有人曾经告诉我当他极度想念已逝之人时,他就在脑海里编个小故事。比如,他会想象死去的朋友其实是在阿拉斯加的三文鱼罐头厂工作,那里很远,不通电话、没有网络。当我十分想念大卫时,我会想象他在罐头厂、小船上或者是热带岛屿上。不久之后他就会回来,我就能见到他了。
葬礼结束后,大卫的父母想让我收藏一些他的遗物。他们送给我大卫的画作,还有一篇论文的复印件。论文是关于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一位十九世纪英国艺术家和评论家的,试图解释拉斯金对于自然的看法是如何改变了我们看待自然的方式。论文的分析将文学、艺术、建筑囊括其中。
在我的书架上摆放着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系列作品和《大卫•科波菲尔》。每当我很久没有想起美丽而充满活力,像朵拉一样英年早逝的朋友时,我就会翻阅这些书。
去年,我遇到了在收容所的一位员工。他告诉我他喜欢这份需要与将死之人和他们的家庭打交道的工作,而且他时常从文学作品中发现智慧,既为己用,也与人分享。他给我看了他随身携带的笔记本,里面记满了他看到的语句。我翻阅着,发现了一句约翰•拉斯金的话:“我不开心时,听歌剧好像是狂风呼号;开心时麻雀叽叽喳喳的叫声都很悦耳。并不是麻雀的叫声让我开心起来,而是因为我的心情让它变得动听。”
当我想起大卫•拜耳时,我要选择怀念他让我开心还是悲伤,是记住他的生命还是死亡?我努力选择开心,努力选择生命。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帕布莉卡 » 《大卫•科波菲尔》怀念 -《为生命而阅读》
 帕布莉卡
帕布莉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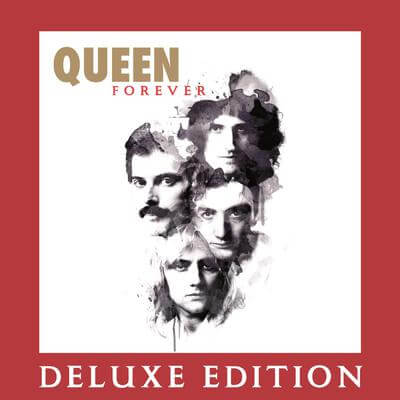 杨炼《老人》
杨炼《老人》  麦姐也玩“七年之痒”,事业之绊导致劳燕纷飞
麦姐也玩“七年之痒”,事业之绊导致劳燕纷飞 明星智商趣谈
明星智商趣谈 玛莎·葛兰姆(Martha Graham)是美国国宝级舞蹈家和编舞家
玛莎·葛兰姆(Martha Graham)是美国国宝级舞蹈家和编舞家 麦当娜语录:性肮脏吗?只有你不洗澡才是
麦当娜语录:性肮脏吗?只有你不洗澡才是 Justin Timberlake《500 Miles》
Justin Timberlake《500 Miles》 爱是一颗心遇到另一颗心(出处+配图)
爱是一颗心遇到另一颗心(出处+配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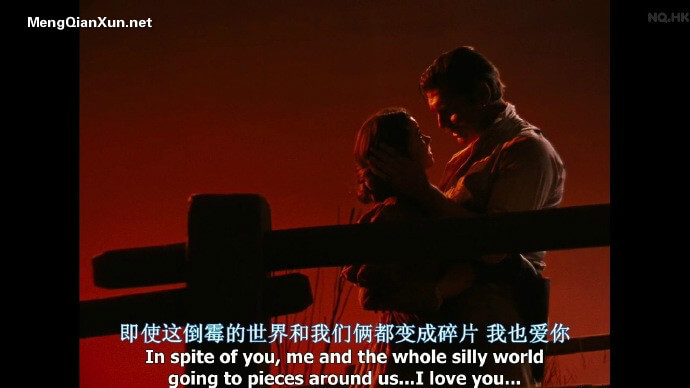 《乱世佳人》电影专题
《乱世佳人》电影专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