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妮娅是我中学同桌,那时候中学生要求必读《钢铁》,读完还要写千字读后感,于是终于得到放心大胆的读课外书的理由。
读罢,我跟她说,你就是冬妮娅。
她还没全读完,她跟我说她觉得保尔在桥上和冬妮娅分手的时候就不是保尔了,是一个无趣、失去自信,丢了魂儿的人。
多年以后,我早已跟冬妮娅失联,有趣的是,在发达的社交网络中找到一个曾经再熟悉不过的人,是再容易不过的事儿。
我觉得我有当猎人的天赋,好猎人一定擅于跟踪、窥视,冬妮娅说她觉得我这人自恋,我说鼻子好使的像狗一样,怎么能不叫自己喜欢?
我们最后的交集留在QQ上,那时候还没有微信呢,相比起朋友圈自带的私密性,QQ空间夹在它与微博之间,成了一个年龄段社交方式的缩影,而很多失联的人,在他们弃用QQ后留下的那些已为陈迹的动态,则凝固成褐色的斑点,带有最后一丝存于风中的血气,我是寻觅这一丝血气的人,只是寻找,随后远观,最后消失。
我的计划是这样的:借由她的QQ号可以找到她的人人网账号,然后顺藤摸瓜,我可能在她的人人网主页上找到她的微博。
十五分钟后,我在饶有兴趣的翻看着K的微博,冬妮娅不玩人人,反倒是歪打正着得到了K的社交信息。
曾经和冬妮娅一起读过有关民国文坛的一套丛书。冬妮娅说她佩服林徽因但又很讨厌她,她觉得她“茶气太重”,但又是个绝顶聪明的女子。
她说,绝顶聪明的人,也分两种,一种是老实人,一种欺负老实人。
很久以后,读了一些为林才女“平反”的文字,总之文人写得东西,永远能说得出理,甚至有人拿《钢铁》里那个正牌冬妮娅和她相比较,他们说她被过度消费,说她是先被过誉,后被过贬。
我只以为,人其实是只愿相信自己所信之事的,即便知晓这个道理到今天,我亦是如此,所以即便早已和冬妮娅失联,她曾说过的某些话尚留在我心中,我是愿意相信的,我就是要找到她,看看她,再决定是不是要问问她。
K在我印象里是个身型高大的女孩儿。念书的时候,校内也是场大戏,有的人是王孙,就有人得扮小丑。K总是被捉弄,性情上大大咧咧里又有几分刻薄,象征性的抗争了一段时间,也就接受了大众对她的心理预期定位:傻。
所以K一方面是安静的,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活在聒噪之中:不起眼,不甘心。如果你也曾是个平凡至极的人,同时内心里又总萌生着一些疯狂的想法,你也会做同样的梦:你从梦中梦醒来,用凉水浇醒疲惫的魂儿,然后瞪视着镜子,你想嗷嗷大叫却只能发出几声哀鸣,因为你的躯壳还是那么不起眼,但你灵魂所承载的特异早就溢出来了,却仍旧挣扎在这份不特异的外皮之中。
这梦对女子更刻薄。世界从来都不平衡,社交网络里总有人把“因为胖被男友抛弃,随后痛下决心减肥几十斤,女屌丝变女神,就为了让他悔不当初…”当励志故事讲,琐碎的像是牌坊下的交头接耳,却又像潮冷小屋中深居的小脚老太,叫人哭笑不得。
冬妮娅和我,都不是爱谈世事的人,因为都爱读书,所以话题又总是不得不绕到世事上,最后我们约法,谈到世事不争,就是凭着个人喜好,说到哪算哪。
即便就一个小小班级,在一群早熟少年的驱使下,也分成了鲜明的两派。她说我是自然人不掺和有的没的,我说我是嘴拙,所以就决定当好石头,别人问我,我就哼哼两声。
冬妮娅可不一样,她人比我灵活的多。看她游说于小小社会中,还真的是有模有样,可她终究是不喜欢这些的,生活还要过得,男人当个石头还可能被说成沉默是金,换个性别好像就不一样了,所以生活还要过得,却过得并不平衡。
保尔带冬妮娅参加工人聚会,两人最后闹得不欢而散,保尔说冬妮娅几年前还愿意大方跟工人握手,现在却对着工人伸来的沾满泥污的手皱眉,放在当今网络里,保尔的做法等同于“直男癌”,却也因为“保尔”这个名字,得以幸免,冬妮娅就要替罚了,人群如饿狼,审判不了的就翻页,总之要审一个,才能解了妒火的渴。
别说冬妮娅一顶干净的女孩儿不爱和满是泥污的手握手,我也不爱。有些泥污,尤其是机油,不及时清洗的话,肮脏油腻,是从中看不出什么“意志”,我当然理解,但我又不想这么简单的解释,冬妮娅她说我是自然人,因为我不一天到晚净整没用的,我说她也是,因为她也不整这些没用的,区别是她灵活,我笨拙,所以当她满含戏谑的游说于人群之中时,她心中怀有着不多的热情以及大部分诟病,我则是唯一的观众,看完然后什么也不说。
K的微博中是一个我几乎不曾认识的女孩儿,她的高大蜕变为高挑,她的脸上是让人舒适愉悦的妆容。她爱美,衣品很好,这都是我们其他人所完全不认识的那个K,而有关于这些年的不易与辛酸,也只留存于她的心中,别人问她,她或可能只会莞尔一笑,轻松的说道
“我那时候看起来好傻啊”
我想起了那时候我们所流传的“一支烟的友情”的故事,大概是从美国某部纪录片中传出来的,所谓“一支烟的友情”,不过是两个高中生下课的时候躲着轮流吸一支烟,可能多了些暧昧的氛围,主角一男一女,但这份情谊确实没越过也不需要越过吸吸烟,聊聊魔幻皮草(The Psychedelic Furs)的音乐的程度,这远比在美国高中广受欢迎的橄榄球星或是舞会女王来得有生命力的多。
我们这不一样,鲁迅说我们固有的一些糟粕文化“一见白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裸体……”,实非虚言。
冬妮娅跟我说,人有一种成熟,到了一个岁数,会变成另一个人,熟悉的人,不顺路也会变成陌路人。过了很多年,我还是觉得她说的不错,这世上总会有人,怕闹,怕人潮汹涌,怕喋喋不休,怕以团结为理由的捆绑,怕以人情为借口的依赖,怕心中存有的连一小时都不能播放而直接被嘈杂人声淹没。
也怕本该自自然然的东西,硬要套上承诺、誓约。
急赤白脸到相拥而泣重复千万遍的人终于把其编为生活的一部分,再精简成回忆。
我心说我是拒绝这样的,麦琪的礼物我看一遍就落泪了然后我一辈子也难忘每一次想想都心酸可是生命有限余味悠长我怎么舍得一口气把动容用光我还是留在心底偶尔拿出来心酸一次感动一次吧。
给冬妮娅看《麦琪的礼物》,她看完也哭了,有些人把这眼泪称为“善良”,多年以后,我们早不用这词来形容人事,却惊觉每次想起这段故事,都有些震颤的心酸,原来疼痛还是会唤醒人初始所拾得的一部分美好,而当舔舐这小小的自怆时,又缓缓的治愈一部分黑暗。
K的关注里有冬妮娅,我之前已经说过了,这么发达的社交网络里,找一个人很容易。
我不是很情愿的点开冬妮娅的微博,我清楚当我点开的一瞬间,我的追猎就将完结。有的猎人是为了谋生,更应该被形容为打猎为生,我不一样,我爱嗅那空气中淡薄的血气,因为当我闻到时,就好像能实现时空穿越一般,时间场景将永远一去不返,气味不一样,总会有熟悉的味道重现,闻到过去的气味,就可以假装回到过去。
冬妮娅只有两条动态,一组照片里她在海滩上,笑得非常开心,后面几张有在台北101的留影。
中学毕业典礼的前一日,我和冬妮娅最后长谈了一次,我们谈所有想谈的,谈几年里发生过的那些最难忘的事情,以及谈到最后发现实在是没什么可说的,却又想找些什么说,好像已经隐隐感受到了某段旅途的终点,而我们了解规则。
最后,她问我对爱情的看待,我说我们不是早就达成一致了吗?她说如果一定有不是友情的爱情呢?我说我大概会离开吧,先是深陷其中,然后某一天突然消失,因为我也不知道从何而始,因何而终。
她说你还是爱你自己,我问她你知道你为什么像冬妮娅吗?
但她没有再说什么,我也没再说什么。
如果可能的话,我想跟她一起刷各种社交平台,一起刻薄,一起把看透的大声念出来做一个令人厌恶的人,一起嘲笑那些把酒当做良药的自以为文艺青年,一起鄙夷那些把生活当做秀场的怒刷存在党,一起戏谑那些深陷于物质与现实巨大割裂而挣扎不出的投机之徒,然后,我们一起撤离,从尘埃中撤离,没人会看见我们,以后也不会。
寂寥了,会再回来,然后再消失,直至如断线傀儡,把魂儿像风一样放了。
毕业典礼我没去,对我来说,毕业典礼已经结束了。那天傍晚我在车站,准备动身去一座陌生城市,我接到了她的电话,她简单的问候了两句,然后她问我想做什么,我说我还是没有想好,她说她想用一个故事来形容我我说好,她说
“我梦见我们都在麦田里,麦田起风的时候男人就要升空参战。你飞的比他们都高,也都远,但除了我之外没人知道你不怎么会降落,告你你也不听,马上要打仗了,别人都在练习,就你在那踢石子儿玩,就在那磨蹭,在那晃啊晃啊,你自己是知道要起风了,但你还是在那磨蹭……”
在照片下面的动态,更新于很久以前,是中学毕业那年的,新裤子的一首歌《总有一天我会欺骗你》
关上灯,我陷于静谧之中,戴上耳机,轻点播放。
在梦里,有些话要说给冬妮娅,如果只是说什么,是否是存于现实,还重要吗?
梦中我来到了故乡那个熟悉的街角,零几年的时候那里起了一座大厦,是个购物中心,挂了四面的巨型广告,如今已经泛黄了。
其中有一副我一直记得,大概是那一年流行概念风格,广告上模特们从太空舱中走出,那么缥缈,又那么接近,可她们现在并不能拒绝泛黄的命运。
我想把这个笑话讲给冬妮娅听,我想问她见过泛黄的太空舱吗。
可到嘴边,似乎又只能嘟囔出什么
“啊,冬妮娅…”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帕布莉卡 » 街角的冬妮娅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帕布莉卡
帕布莉卡


 爱是一颗心遇到另一颗心(出处+配图)
爱是一颗心遇到另一颗心(出处+配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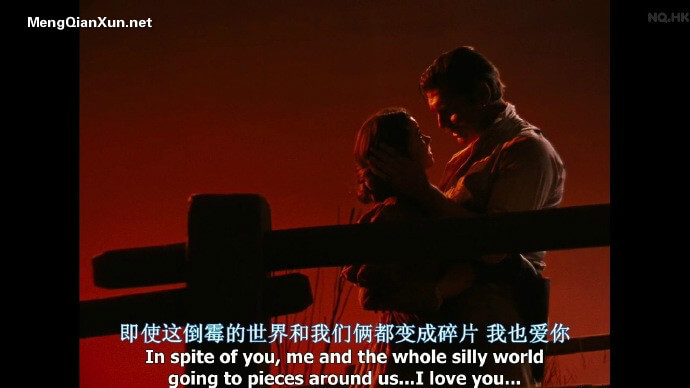 《乱世佳人》电影专题
《乱世佳人》电影专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