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汤达:人的激情——心理的描绘者
司汤达的审美心理机制
司汤达处在科学主义刚开始盛行的时代,他自然要受其影响。不过,在哲学上,他接受的并不是风行一时的实证论,而是孔狄亚克和爱尔维修的唯心论。在自然科学方面,他和深深地影响了其他19世纪现实主义作家的生物学、解剖学、遗传学等相距甚远。他倒是研究过生理学和有关人的气质的理论,尤其是对人的气质的研究,加上在先天的心理和生理气质上“司汤达明显是内省型的”,致使他在日常生活中倾注于对人的欲望、情感产生之规律的研究,使他养成了热衷于观察人的心灵世界之奥秘的习惯。他曾立志做一个“人类灵魂的观察者”,并以之为荣。由于他天性中的内省特征,在对人的心灵的研究上,他首先是从观察和研究自己的心理开始的。他很能体会自身的心理变化,并能无情地解剖自己的阴暗心理。他的《情爱论》以及日记、笔记、书简等记载了许多此类自我观察、内省和解剖的内容。他在1811年的日记中写道:“这样的人应该从窗户里扔出去。”这是他对自己下的评语。在自我观察的基础上,他又由此及彼地去研究他人的心灵。正如美国一位司汤达研究者所说:司汤达“能够全身心地去感应所有合乎于自己潜在天性的事物,去探究自身的这种潜在天性,并以这种方法去掌握别人的内心体验”。平时,“他始终保持着心理分析家的好奇心,任何灾难风险,疲劳困倦,都没能转移他的注意力”。难怪卢那察尔斯基说,司汤达十分重视心理的科学分析,“他虽然穿着艺术家的外衣,却依然不失为人的天性研究家”。可见,在认识和感知世界的方法与态度上,司汤达虽然同后来的巴尔扎克等作家一样追求细致地观察和研究生活,但侧重点在人的心灵世界上,其“瞳孔”是向内的。
这种对生活的独特感知方式,必然使他的艺术审美情趣趋向于人的心灵世界,形成带有内向性的艺术观。他在著名理论著作《拉辛与莎士比亚》中不是竭力推崇莎士比亚吗?那是因为他认为,莎士比亚的悲剧不仅真实地描绘了外部世界,而且“大量地描绘了人的心灵世界的激荡和热情的最细腻的千变万化”。“莎士比亚很懂得人的心灵。莎士比亚的作品中,任何喜怒哀乐,任何情感,他都能以一种令人赞赏的真实情态细致入微地描绘出来。”司汤达在评价莎剧《麦克白》时还说,剧中“所表现的这种人类心灵的热情变化,就是诗在人们面前最辉煌的展示,而且这种诗深深打动了人也教育了人”。他对拉辛之所以有所否定,主要原因是拉辛的悲剧“从来不写激情的发展过程”。很明显,司汤达所关注的是真实地表现人的心灵世界。通过文学展示人的心灵深处之奥秘,是他对艺术创作的一种潜在的心理欲求。他的审美心理机制是内向型的。
注重人物心路历程的描述
无论在司汤达的长篇还是中短篇小说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司汤达十分注重描写人物心理变化的过程,人物的心理冲突往往是小说的内在情节:作者细致地展示人物情感和心理的细小单元,仿佛是通过显微镜使细微的细胞都清晰可见,而这一连串情感和心理的细小单元结成一个整体,就构成了人物性格,因而,在展现人物心路历程的过程中,人物性格也得到了展示;与此同时,又较为充分地再现了人物赖以存在的外部世界,因为作者总是将人物的心理冲突放在一定的社会心理背景上展开的,人物的心理冲突,又往往是人与外部社会的冲突在心灵中的投影。所以,司汤达尽管有时也放手描写人物的外部冲突和外部世界,但其归宿始终在表现人物的心灵世界上。难怪勃兰兑斯和朗松说,“司汤达全神贯注心理学现象,把其他一切置之度外”,“什么环境描写、人物外貌、自然风光,在司汤达小说中几乎不占位置”。
《阿尔芒斯》是司汤达第一部成名作。小说描写的核心内容就是阿尔芒斯与奥克塔夫的情感、心理冲突。奥克塔夫出身贵族,但一向蔑视金钱、地位,厌恶上流社会的生活。当他知道贵族小姐太太们因为他将得到两百万巨额赔款才对他大献殷勤时,更增强了对上流社会的恶感。然而他发现在众人当中,表妹阿尔芒斯却没有向他献殷勤,因而觉得在这个上流社会中“仅有她一人有高贵的心灵J于是,他内心对她产生了敬意,以后又深深地爱上了她。但他曾发誓不结婚,另外他还不知道表妹是否也爱他,并且是否也因为他有巨额财产才爱他,因而他竭力克制自己的感情。这样,他的内心深处始终存在着爱与不能爱的心理冲突。阿尔芒斯是个寄人篱下的孤女,但心灵高尚,不为金钱所主宰。共同的思想基础,使她在心底里爱上了表哥奥克塔夫。但是,她又担心表哥自恃有地位和金钱,看不上她这个穷“伴娘”;同时又担心旁人说她为了金钱和地位才爱奥克塔夫,从而给她以无端的嘲笑和攻击,所以,表面上她对他总是十分冷漠。当奥克塔夫亲近她时,她还故意说自己已和别人订婚了。她的内心深处,也始终为爱与不能爱的心理矛盾所骚扰。从本质上讲,他俩的思想、情感是基本吻合的,因而他们的心理距离本该是很近的。但是,环境因素的影响,使得这两颗心灵既互相吸引又互相排斥,心理距离时近时远,他们相爱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成了爱与不能爱的心理演绎过程,他们的心灵,始终处于骚动不安的状态中。由于这种心理演绎是在那崇拜金钱、趋炎附势的特定社会心理氛围中展开的,因此,在描写人物心理历程、展示人物性格的同时,又再现了当时法国上流社会的风貌,有内部世界的表现,也有外部世界的再现,而前者是占主导地位的。
《红与黑》是司汤达的代表作,从外在情节看,小说描写了于连在三个不同环境中不平凡的生活经历,因而深刻反映了19世纪上半期法国的社会风尚。但更深入一层可见,小说着重描写的是个人奋斗者于连的心理演变史。他出身低微,在环境的重压下,强烈的自我意识在他的心灵中酿成了自尊与自卑、虚伪与正直、雄心与野心、反抗与妥协等多重心理矛盾。从当家庭教师到被送上断头台这短暂的生活经历,实际上是他内心多重矛盾交替展开的过程。在瑞那市长家,主要是自尊与自卑的冲突;在神学院中,主要是虚伪与正直的冲突;在木尔侯爵府中,主要是雄心与野心、反抗与妥协的冲突(当然每个阶段中多种矛盾冲突有时是同时展开的)。由于内在心理冲突的复杂性,于连的心理流程显得格外蜿蜒曲折、深不可测,所展示的性格也就异常复杂。瑞那夫人和玛特儿小姐虽然不是小说的中心人物,但围绕着中心人物于连所展开的心理冲突同样展示了她们心理演变的“轨迹”。这三个重要人物之间展开的心理冲突,又构成了小说的内在情节,成了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
《巴马修道院》是司汤达小说中描写社会场景最为雄伟壮阔的长篇,但即使在这部作品中,中心内容仍是人物心灵世界的展示。小说中泼墨最多、写得最精彩的,并不是炮火连天的拿破仑
征战场面,也不是钩心斗角的巴马宫廷的官场角逐,而是法布里斯、吉娜和克莱莉亚心灵的痛苦与欢乐。法布里斯和吉娜感情至深,但他们之间由道德观念造成的心理障碍使各自处于感情的奔突与理性的束缚带来的心理矛盾之中。克莱莉亚和法布里斯倾心相爱,但政治和宗教的围墙又把他们隔开,各自处于爱而不能的感情与心理动荡之中。这三个人物的情感与心理的变迁是小说描写的主干部分。
与上述作品相仿,长篇小说《吕西安・娄凡》、短篇小说《法尼娜法尼尼》等,描写人物心理变化过程同样占重要地位。
做以上分析,并不意味着对司汤达小说中的外部描写以及所表现的深刻的社会内容视而不见,而旨在说明:司汤达小说描写的侧重面是人物心灵世界的变化过程,外部世界是在展示心灵世界的过程中得到表现的。如果我们不只是满足于用社会学、历史学的眼光,而是更多地以艺术的、审美的眼光去观照司汤达的小说,那么,就不能不承认:细致地、真实地展示人物情感和心理演变的过程,使司汤达小说产生了很强的艺术魅力,因而也获得了很高的美学价值;多少年来,司汤达小说的备受欢迎,主要原因也在这里。其实,承认这一点,并无碍于我们发掘司汤达小说之社会学历史学价值。
披露人物的深层心理
也许,司汤达自己也不甚清楚,他为什么能将笔下人物的心灵之骚动不安、激情之剧烈奔腾写得那么透彻入微。要是他生活在心理科学高度发展的20世纪,那就定然明白,这是因为他在描写人物心理历程时,触及了人的深层心理——潜意识与前意识。这正是作为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司汤达描写人物心理的深刻之处。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认为,人的心理结构分为意识、前意识与潜意识。这里,弗洛伊德虽然夸大了人的心理结构中潜意识的容量和性本能的作用,但潜意识和性本能的存在是毋庸否认的。尤其是性本能所导致的“欲”,它作为人的内在生命力的一部分,潜伏于潜意识中,通常也并非均表现为恶。在外力的刺激下,它会上升为前意识中的“情”情”是一种长期积累着的情绪记忆,它可以被意识到,但平时只作为一种信息贮存于大脑之中,其中大部分又回归于潜意识领域。“情”以“欲”为本源,并常和“欲”相交融。同“欲”与“情”相对应,意识层次中存在着由各种社会性内容积演而成的“理”,它是可以被人感觉到的。司汤达笔下人物心理的冲突,往往是在“理”、“情”、“欲”这三个心理层次间展开的。
德瑞那夫人与于连之爱有漫长的心理演绎过程,其源头可以追溯到他们最初见面之时。当时,瑞那夫人已经是有两个孩子的母亲,但是,她却从未体验过真正的爱情,并且,她笃信基督,向来把小说中的男女之爱视为邪恶的表现。在于连到她家之前,她想象中他定是个满脸污垢、粗鲁不堪的人。其实,19岁的尚未涉足爱情的于连是个眉清目秀的“美男子”。当他带着“少女般羞怯”的表情第一次出现在市长夫人跟前时,她发呆了,继而心里“充满少女的疯狂的快乐”,“她只看见于连鲜明俊秀的面色,大而黑的眼睛,漂亮的头发,便为他迷住了”。与之相似,于连第一眼看到瑞那夫人时,“被德・瑞那夫人的温柔的眼睛吸引住了,也忘记了羞怯,立刻,更惊奇的是她的美丽”,接着,于连又闻到了瑞那夫人“夏季衣裳的香味,这对一个穷苦的乡下人来说,是怎样的惊愕啊!于连面红耳赤”。他觉得,这个年逾30的贵妇人“只是20岁的少女”!在这一段内与外的描写中,作者把男女主人公推入一种他们自己都不曾意识到的潜感觉中:
他们都不由自主地为对方的外貌、情态所吸引,客观的信息成了主观的感觉流程。他们“呆”、“乐”、“着迷”、“惊”、“惊愕”、“面红耳赤”等情态的变化,显示了各自潜意识中“欲”的萌动。相比之下,这种“欲”在于连身上显得更突出。作者接着写道:于连“立刻产生了一个大胆的念头,想吻她的手”。但是心里又害怕。吻手的念头是“欲”的进一步外现;而“理”的抬头则使他害怕,阻挠了“欲”的外现。但害怕之后于连又立刻想道:“难道我是个无用的低能儿吗?我无用到了这个地步,不能做一个对我很有用的动作吗?也许,这个动作可以减少这个贵妇人对我的轻蔑。”这是于连强烈的自我意识的显现。自我意识是人的个体生存本能与社会环境冲突的产物,长期受社会迫力的作用,曾被挤压在前意识中,一有机会就会显现出来。于连由于从小说受社会、家庭的压迫,因而自我意识格外强烈,当他的头脑中一出现“无能”、“轻蔑”等词时,自我意识很快被澈发出来,这是自我意识与“欲”之合力的作用,使刚刚还感到害怕的于连随即“大胆地拿过瑞那夫人的手送到自己的唇边”。对瑞那夫人来说,于连的这一大胆举动,使她“大吃一惊”,觉得“应该生气”,但又很快就“忘记了刚才害怕的事儿”,她对于连根本不存在责备之心了。她的“吃惊”是很自然的,因为像她这样一个贵妇人,“理”的力量是远超过于连的。然而她很快又“忘记”了,这似乎不合理性逻辑,但却符合情感逻辑:由“欲”上升到前意识的“情”主宰了她的心灵,行为也就由感情所操纵。以上的描写,均因显露了人物心理的深层内容,才使人感到男女主人公情感、心理及外部动作、情态的变化入情入理。以后,于连和瑞那夫人之间的爱的心理演绎无论冲突如何激烈,都是以上述心理冲突为原型展开的。于连在花园里出于“责任”第一次把瑞那夫人的手握住,从心理内容上看,主要受前意识中自我意识的驱使,但也受“欲”的鼓动。至于瑞那夫人,对此,她先是“努力缩回”自己的手,继而由于“欲”和“情”的逼攻,她又让自己的手“留在于连手里”,接着又主动地“将她的手送给于连”。这里,人物外部动作的幅度是细小的,但心灵的起伏、情感的流动是大幅度的,其内在原因是深层心理能量的释放。当于连深夜潜人瑞那夫人的房间时,双方心灵中表现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剧烈的矛盾冲突,这主要是他们心理结构是“理”与“欲”搏斗造成的。经过漫长的心理演绎之后,他们各自心理结构中“情”的领域扩大了,“欲”的成分减少了,“理”的力量也进一步减退。于是,他俩的心灵趋于平静,他们坠入了倾心相爱的情网之中。到最后,“理”的力量近乎消失,“欲”则高度升华为“情”,他们心灵的冲突和情感的奔突平息了。所以,于连身陷囹圄,他们倒是心心相印,恩爱之情表现出超常的温柔、宁静与优美!总之,在于连和瑞那夫人感情和心理波涛的涨落中,深层心理内容的外现是很明显的。
于连与玛特儿小姐之间的爱的演绎,一开始表现为虚荣、骄傲、自尊、自卑等理性内容的冲突。尔后,他们潜意识中的“欲”逐渐显现,且越来越强烈,而又极少上升为“情”。因此,他们之间的心理冲突主要是在“理”与“欲”之间展开的,他们之间的感情也就决没有于连和瑞那夫人那种真挚、宁静和优美,而是狂热有余而真诚不足,野性有余而温情不足。所以,司汤达自己也认为,前者是“心坎里的爱”,后者是“头脑里的爱”。这种细微差别的显现,也在于披露了人物之深层心理。
在《巴马修道院》中,法布里斯与吉娜的感情虽然没有发展到于连与瑞那夫人那种程度,但就心理冲突的方式而言是基本相似的。只是,由于他们之间的血缘关系的存在,使各自心理结构中“理”的力量特别强大,足以抑制“欲”的充分外现,“欲”被挤压在前意识和潜意识中,难以达到高度升华,因此,他们的“情”中总是包含了强烈的“欲”。他们总是不时地感到自己爱上了对方,但又只能竭力克制,每逢此时,他们心中有欢乐,但更多的是受压抑造成的忧郁、痛苦甚至狂乱。法布里斯去法国后,吉娜觉得“到湖边散步还有什么意思呢?”而法布里斯回来后,她总是“对什么事都感到强烈的兴趣,总是那么活跃”。当法布里斯拥抱她时,她高兴得“泪如雨下”。以后她发现他和克莱莉亚相爱,内心痛苦不已,时而表现出对克莱莉亚的憎恨之情。吉娜对法布里斯虽有很深的“情”,但其中有强烈的“欲”。正因如此,才使读者始终觉得她对他的感情是远超出作为姑妈对侄子的感情的。法布里斯也一样,他爱吉娜,渴望和她待在一起,但又觉得应该远离她;而远离她时,他又“对她有了他对任何女人都不曾有过的爱情,再没有比永远分离叫他难受了”。在这种情形下,“欲”与“情”不断地企图外现,但又遭到“理”的抗拒,因而导致了他在压抑、忧闷、狂乱之下竟为争夺一个39岁的女戏子,同流氓吉莱争风吃醋并杀死了对方。从内在心理动因看,这完全是因为“欲”与“情”的膨胀而又得不到释放导致心理失常所造成的。短篇小说《法尼娜法尼尼》中的法尼尼,也是因为心理结构中“欲”与“情”的膨胀才使自己的行为走向了爱的极端。
在《吕西安・娄凡》、《阿尔芒斯》等作品中,人物心理冲突的形式略有不同。潜意识中“欲”的显现较为隐晦,“情”的领域也不显得特别庞大。理、情、欲三种心理能量趋于基本均衡,因而,心理的变化、感情的涨落和性格的变迁较为平稳。无论是吕西安、夏斯特莱夫人还是奥克塔夫、阿尔芒斯都是这样。
对司汤达来讲,披露人物的深层心理,尤其是潜意识,并不是一种自觉的目的,他也不可能有这种自觉意识,除非弗洛伊德早诞生一百年!但是,由于司汤达长期倾注于人的心灵的研究,而且他在创作中是通过“自我分析把它反映出来”的,因此,在描写人的内心世界时,对心理变化把握得格外精细,能够较为深刻地揭示人物心理变化的内在动因——潜意识与前意识,从而使人物心理的描写真实、细致、可信。这说明,人的潜意识与前意识也属于艺术美表现的范畴。如果作家能自觉地、有分寸地把握人的深层心理,同时又不切断心理的“外接天线”——环境因素,那么,对真实地展现人的心灵世界之奥秘,发掘人的心灵世界之美,是十分有益的。
把注意力集中在性格“自己运动”的泉源上
现实主义文学在人物塑造方面要求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但这并不是说性格必须由环境决定。唯物辩证法认为,研究事物变化应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自己运动”的泉源上。因为,“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任何事物内部都有这种矛盾性,因此,引起了事物的运动和发展。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则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原因”。这说明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就人物性格来讲,它的形成和发展必须以环境为前提,但根本原因则在性格自身的矛盾性。从系统论的观点看,人物性格作为一个开放性系统,具有自组织自调节能力,它虽受环境的作用因而存在自在性的一面,但对环境又有一种超越力量,因而具有自主性,也即“自己运动”的能力。所以,性格并不是被动地接受环境的作用而作为环境的引申物存在的。司汤达笔下的主人公形象往往具有很强的自主意识,他们总是处在同环境奋力抗争的情境中;他们的性格不是在典型环境中生成的,而是在典型环境中得到展示和强化的;性格和环境虽然有联系因而具有自在性,但性格的衍变基本上是按自身内在的逻辑,在内动力驱使下进行的,而不取决于环境的影响,所以自主性超越了自在性。
于连是司汤达小说中塑造得最为成功的典型。在当家庭教师之前,他的性格就已基本形成,因此可以说是既定的。在维立叶尔城、贝尚松神学院和木尔侯爵府这三个典型环境中,既定的性格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和强化。因而,性格与环境之关联并不表现为环境对性格的决定作用,而表现为环境促进性格的展现,环境只作为展示性格的条件、前提或外迫力而存在。于连从小受父兄的歧视,但他从不屈服,反抗性就在这种环境中孕育而成。儿童时代他受拿破仑思想的熏陶,渴望凭自身的聪明才智出人头地,并下决心“冒九死一生的危险也要发财”。这说明个人奋斗的性格也是早已有之的。反抗性和个人奋斗是于连性格的总特征。走向三个典型环境后,于连不是环境的奴仆,而是自我的主人,直到生命终止,他那既定的反抗性和个人奋斗性格并没有因环境的“影响”而改变,相反是表现得更为鲜明具体。由于他的这种性格是不见容于那个社会的,所以,他的一生奋斗,实际上是性格同环境激烈抗争的过程,正是在这种抗争过程中,性格才得以展示和强化。这里,既有性格抗拒环境而“自己运动”的自主性,又有性格和环境关联的自在性,并且,自主性是超越自在性的。
当然,于连性格实际上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除了反抗性与个人奋斗之外,还存在着其他一些性格元素,但这些元素也都带有既定的成分。
《阿尔芒斯》中的奥克塔夫一出现在读者眼前就是个蔑视金钱、清高自傲,与盛行拜金主义、趋炎附势、虚荣伪善风气的上流社会格格不入的叛逆者形象。作者描写他所处的环境,主要并不着意于用它来说明主人公叛逆性格如何受环境影响而形成,而是为人物提供一种社会心理和精神的氛围,为展示人物心理和性格提供外在条件或依据。所以,奥克塔夫在行动上总表现为我行我素。环境修正不了他的既定性格,性格也抗争不过环境,因而悲剧就在所难免了。这个悲剧正好说明他性格的自主性对自在性的超越。
在《巴马修道院》、《吕西安娄凡》和中篇小说《贾司陶的女主持》中,主人公生活的时间跨度虽然较大,经历也很丰富,但人物性格是按既定指向发展的。《巴马修道院》第一部写法布里斯毅然离家投奔拿破仑,第二部写他大胆地从高180尺的法尔耐斯塔牢逃出,最后写他疯狂地追求已婚的克莱莉亚等,这一系列行动无不是在他那大胆、果断、富于冒险精神等既定性格因素作用下展开的。吕西安一开始就是个不满现实、追求真诚、有叛逆精神的贵族青年。他经历了在外省从军到回巴黎从政等重大的生活转折,环境的变迁是十分显著的,但性格的基本形态一如既往。小说在最后写道:他“还是不改坏习惯”(这里的“坏习惯”指他不和上流社会之虚伪卑鄙同流的那种叛逆性格)。复杂的环境只起说明和展示性格的作用。《贾司陶的女主持》中的虞耳那“强盗”的性格也是在他同环境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中得以展示的。
司汤达小说中人物性格自主性对自在性的超越,说明了作者在塑造人物上,一方面揭示了性格的外部联系,另一方面又不迷恋于外在因素的描写,而是侧重于性格内在动因的探寻,始终把注意力集中于性格“自己运动”的泉源上。这一特点的形成是和作者注重人物心路历程的描写一脉相承、互为因果的。因为,他笔下的人物性格总是在表现心路历程中得到刻画的。注重心理历程的描写必然倾向于性格内在动因和自主性的探索;反之,注重性格内在动因和自主性的探索,必然倾向于揭示人物的心理演变过程。司汤达的这种塑造人物的手法,归根到底又是由他那内倾型审美心理机制决定的。所以,性格自主性对自在性的超越,把塑造人物的注意力集中于性格“自己运动”的泉源上,正是司汤达小说内倾性在又一意义层次上的表现。
以上论述的三个方面,在司汤达同时代的19世纪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只是,表现得如此集中、普遍,首推司汤达。所以,这种内倾性正表现了司汤达小说之独特风格。
几点启示
作为19世纪欧洲批判现实主义的奠基人之一,司汤达小说之内倾性风格意味着什么呢?
第一,它说明司汤达的创作并未给后来的作家提供纯客观地摹写外部世界的样本;他是既真实地再现外部世界,但又以表现内部世界见长的杰出的19世纪现实主义作家。如果说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中存在着内倾性与外倾性两种倾向的话,那么,司汤达无疑是前者的创始人。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则是和司汤达同类型的作家。不深入研究这些作家艺术地把握世界的独特方法,就不可能准确全面地认识现实主义的全部内涵。
第二,它说明19世纪欧洲现实主义文学从一开始就是注重内部世界的描写的。对此,以前我们许多研究者是认识不足的。
第三,它说明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存在对立但并不意味着相互间的隔绝。通常认为,现代主义文学是一种“向内转”的文学。我们上述论及的司汤达小说的内倾性,自然和这种“向内转”有某种程度的契合之处。不过,指出这一点并无意于要把司汤达尊为现代主义的祖师,而是想说:内倾化的艺术表现并不完全归属于现代主义,要不然,司汤达只好被拒之于现实主义大家庭的门外了。既然如此,我们就不能不承认司汤达的创作和现代主义文学之间的客观联系。其实,放眼世界文学的大系统细加考察,谁能说司汤达的内倾性对普鲁斯特、亨利詹姆斯、福克纳等现代主义作家毫无影响呢?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帕布莉卡 » 【读书笔记】《十九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现代阐释》 -司汤达:人的激情——心理的描绘者
 帕布莉卡
帕布莉卡


 爱是一颗心遇到另一颗心(出处+配图)
爱是一颗心遇到另一颗心(出处+配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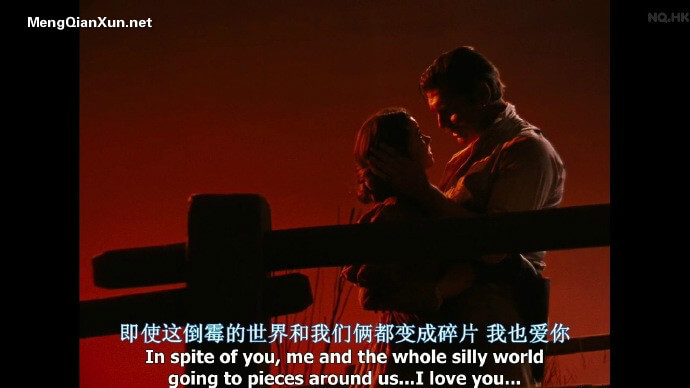 《乱世佳人》电影专题
《乱世佳人》电影专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