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莫尔索到克拉芒斯,
世界还是那个糟糕的世界,
人也还是那么糟糕的人。
我们很少信任比我们好的人,这可太真实了。我们宁肯避免与他们往来。相反,最为经常的是我们对和我们相似、和我们有着共同弱点的人吐露心迹。因此,我们并不希望改掉我们的弱点,也不希望变得更好,我们大概首先应该被判犯了错误。我们只是希望在我们的道路上受到怜悯和鼓励。
——加缪《堕落》
THOUGHTS
《堕落》
阿尔贝·加缪
看名字,不是很理解为什么存在主义哲学家,无论是萨特的《恶心》,还是加缪的《堕落》,都给人直观上一个简单的负面词汇作为书籍和文章的标题。
深入阅读后,发现这是一种类似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的行文,但没有地下室狂人那么语无伦次。他们都是借主角之口表达作者的思考和批判。如果说萨特的恶心是借由主角的卑劣作为靶子让读者批判,那么加缪的批评更加尖锐和刻薄,某种程度上把包括读者在内的所有当时欧洲的年轻人人性的恶和虚伪都批判了进去。
开端是主角克拉芒斯与人喝酒谈天的第一视角,可以说是一个人醉酒后的胡言乱语和谈天说地。其实听者对方是谁不重要,作者是借这样的机会和所有读者“谈天”。在主角单方面表达的时候,主角的讽刺,对自己的审判和明褒暗贬,对两性关系的分析和“不经意”展露出来的洋洋自得,不止是在批判当时欧洲社会的年轻人,其本身更是值得批判的年轻人自己:
对于爱情和对爱情的需求感,加缪说“反正我感到一种暗暗的痛苦,某种使我变得更加空虚的匮乏,它使我半是被迫、半是好奇地承担某些义务。既然我需要爱和被爱,那我就认为自己陷入了爱情。”直指人因为空虚和被需要的痛苦才被迫承担爱情的义务,而非出于本心。
对于虚伪的善良和同情,只是人们为了展示自己道德上的一种手段,加缪说:“当我照顾他人的时候,那是纯粹的屈尊低就,我有完全的自由,而全部功劳又回到我的手上:我在我的自爱中又升高了一级。”看啊,虚假的同情是为了成就道德上的自我超越,而非真的同情弱者。弱者只是完成人们完成自我安慰“自己是个善人”的工具而已。那些我最常帮助的人,是最受轻蔑的人。同情帮助的行为改变不了心底发出的蔑视。
对于奴役和人的统治欲,控制欲,加缪说“一句话,能够发怒而另一个不能顶撞,这是根本的。”这是奴役的本质,与同为存在主义哲学家的萨特诉说的人际关系是奴役与被奴役是相似的观点。当时欧洲传统的世俗伦理让最底层的人们都拥有妻儿和宠物,而无论他们在社会评价中是多么贫贱,他们对于妻儿宠物的态度都是居高临下的掌权者,他们热衷于控制和俯视,在家庭关系的主体性掌握主动,剥夺了他人的自由。
存在主义兴起的年代经历了“上帝已死”的思想和批判纯粹理性。人们失去值得供奉的上帝,失去了道德意义,同时也失去了罪恶感的审判。加缪提出了另一个思路,通过主角之口成就了一个“先忏悔受审,是为了审判其他人”的形象。
他说“我们不能肯定任何人的无辜,却可以肯定一切人的罪状。每个人都是他人的罪行的见证。”加缪如果是个律师,他的思维是超前的。他揭露虚伪的审判的逻辑是:“既然人不审判自己就不能判决别人,那就得自己攻击自己以获得审判别人的权力。既然任何一位法官有朝一日都得成为忏悔者,那就应该走相反的路,当忏悔者,以便能够最后成为法官。”这是一种以退为进的战术,放在今天的社会可以说是摆烂的前身:“是啊,我就是烂,我承认,但你又好到哪里去?”只要抛弃道德,自我审判就可以成为锐利的武器。
很有意思的是,他总结性的一句发言“人类最高的痛苦是没有法律而被审判。”可以说是另一本加缪式名著《局外人》这本小说的主旨。莫尔索没有因法律被审判,而是不信宗教,桃色流言,甚至没有因母亲去世而哭泣这种事被判死刑。这是何等的讽刺。
加缪对于虚伪的无情讽刺,以及描绘出来的,表现出的自我反思和从反思中假装不经意流露出的优越(某种做作的凡尔赛),在近百年后的今天依然存在这样的人。
『主角克拉芒斯职业光鲜,却道德败坏,而他的道德败坏,虚伪,自傲,风流,却是自我忏悔下的产物,如果他没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我们便看不到这些忏悔。他既是忏悔者,又是审判者;既是下贱者,又是高尚者。他因虚伪的表象被人敬仰,又因自我忏悔的罪行被读者唾弃,但他又因为自我忏悔的行为值得人尊重,可最后,他确实因为“面对芸芸读者自我忏悔而成为高尚的人”这一点获得内心的愉悦。我们很难用片面的,好和坏,善良和邪恶,高尚和卑贱评价他。他可以同时是高尚的,和卑贱的人。』
如一篇书评写到的:“克拉芒斯的问题是时代的流弊。这是一个道德沦丧、信仰迷茫的时代,意义早已沦陷,理想也已远去。克拉芒斯深埋心底的想法是这个时代大部分人的想法。差别就是克拉芒斯的觉悟,而芸芸众生还执迷不悟。”
引自:https://www.sohu.com/a/238393824_699530
部分摘录:
纵情使性,这是大型动物的特权。
当人们或是出于职业需要,或是出于天性,就人这类生灵沉思良久之时,往往会怀念起灵长类来。它们是不打小算盘的。
我知道爱好精致的袜子并不一定意味着有一双肮脏的脚。尽管如此,风度却和常常掩盖着湿疹的府绸衬衣相似。我对自己说,无论如何,聊以自慰的是,说话结结巴巴的人也并非纯洁无瑕。对,还是喝酒吧。
我有时梦想着未来的历史学家将如何评说我们。对于现代人,一句话足矣:通奸和读报。
虚拟式未完成过去时皱眉头,事实上就证明了您的文化程度,首先是因为您知道它,然后是因为它又使您厌恶。
我爱这里的人民,他们挤满了街道,夹在房屋和水之间的狭小空间里,被雾、冰冷的土地以及像洗衣盆一样冒着气的大海包围着。我爱他们,因为他们是双重的,他们在这里,同时又在别处。
法律的观念,因有理而感到的满足,自尊自重的喜悦,亲爱的先生,这是我得以站住或前进的强大动力。相反,如果您剥夺了人的这些东西,您就把人变成了疯狗。
更为罕见的是,我从未同意去奉承任何一位新闻记者,为了使他对我有利;以及奉承任何一位官员,他的友谊可能会有用处。我曾有幸两次或三次被授予荣誉勋位,而我以一种谨慎的尊严拒绝了,我从这种尊严中得到了真正的奖赏。
在我们的社会里,贪婪代替了宏图大志,这始终引我发笑。
我由着自己的天性,任其发展,我们都知道幸福即在于此,尽管我们为了彼此相安无事,有时以自私自利为名装模作样地谴责这些乐趣。
生活,其存在和赠与,迎面而来;我以一种善意的自豪感接受此种敬意。事实上,由于这样充实、淳朴地做人,我觉得自己有些超人的味道了。
请跟我喝酒吧,我需要您的同情。
我嘛,我学会了只满足于同情。这更容易得到,又不承担任何义务。“请相信我的同情”,心里这样说,紧接着就是“而现在,咱们谈别的事吧”。
这是一种议会议长的感情:廉价地得到,然后就是灾难。友谊,就不那么简单了。需要长时间的、艰苦的努力才能得到,一经得到,就无法摆脱,必须正视。尤其是不要以为您的朋友每天晚上都给您打电话,他们本该如此,这是为了想知道您是否正好那天晚上决定自杀,或更简单些,您是否需要有人做伴,是否不能出门。不,如果他们打电话,请放心,肯定是那晚上您不是独自一人,而生活又是美好的。自杀,倒不如说是他们把您推向它,据他们说,是出于您对您自己所承担的义务。亲爱的先生,上天使我们免于被朋友抬得过高!至于那些出于职责而爱我们的人,我想说父母们,他们算亲属(什么样的用语啊!),所以又当别论了。他们有“必须”这一字眼,但是,不如说这个词成了子弹;他们打电话犹如打冲锋枪。而他们瞄得很准。啊!巴才纳之流!
你知道为什么我们总是对死人更公正、更宽宏大量吗?原因很简单!对他们没有义务。他们让我们自由,我们可以从容不迫,把尊敬穿插在鸡尾酒和可爱的情妇之间,一句话,在闲暇之中。如果他们强迫我们什么,那就是怀念他们。然而我们却是健忘的。不,在我们的朋友中,我们爱的是刚刚死去的人,痛苦的死者,我们的悲恸,最后是我们自己。
人就是如此,亲爱的先生,有两副面孔:既爱别人又爱自己。
他们需要悲剧,有什么办法,天性如此,这是他们的开胃饮料。
我认得一个人,他把一生的二十年奉献给一个轻薄女子,他为她牺牲了一切,友谊、工作,甚至一生的体面,却在一天晚上发现自己从未爱过她。他厌倦了,一句话,像大部分人一样地厌倦了。他为自己硬造了一个复杂悲惨的一生。应该发生点什么事,这就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人类承担义务的原因。应该发生点什么事,哪怕是没有爱情的奴役、战争或者死亡。
我很知道人们离不了统治别人和被别人服侍。每个人都需要奴隶,如同需要纯洁的空气一样。统治,就是呼吸,您同意这个观点吗?甚至命运最不济的人也能够呼吸。社会阶梯最底层的人还有其配偶和孩子呢。如果他是光棍,他还有条狗。一句话,能够发怒而另一个不能顶撞,这是根本的。“人不能顶撞他父亲”,您知道这句话吗?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句话不可解释。在这个世界上,不顶撞他爱的人顶撞谁呢?但是从另一种意义上说,它又是令人信服的。应该由一个人说了算。否则,任何一种道理都可以有另一种道理与之对立,这样就会没完没了。相反,实力解决一切。我们花了时间,明白了这一点。例如,您该注意到,我们古老的欧洲终于用正确的方法来推究问题了。我们不再像幼稚时代那样说:“我这样想。您如何反驳?”我们表达得清晰了。我们用通告代替了对话。“这就是真理,我们说,你们尽可以讨论,这我们不感兴趣。但是,几年以后,将有警察,它将向你们表明我有理。”
这完全是句知心话,奴役,最好是微笑的奴役,实在不可避免。但是我们不能承认。不能没有奴隶的人,他们称奴隶为自由人不是更为有利?首先是为了原则,其次是为了不使他们失望。的确应该给他们这种补偿,不是吗?这样,他们将继续微笑,而我们也良心安宁。
我只承认我的优越,这就解释了我的善意和坦然。当我照顾他人的时候,那是纯粹的屈尊低就,我有完全的自由,而全部功劳又回到我的手上:我在我的自爱中又升高了一级。
战争、自杀、爱情、苦难,当环境迫使我去关心,我当然关心了,然而是以一种彬彬有礼、浮光掠影的方式去关心。有时,对一宗与我日常生活无关的案子我装作充满激情。但我的心并未参与进去,当然了,除非我的自由受到妨碍。怎么跟您说呢?悄悄地溜了。是的,一切都悄悄地从我身上溜了。
因此,过一天算一天,我的生活只有一种持续性,即我,我,我。过一天算一天,搞女人;过一天算一天,行善或作恶;过一天算一天,如同狗一样;但是,每一天都是我,坚守岗位。我就这样浮上了生活的表面,某种程度是在口头上,从来也不是真的。所有那些几乎没有读过的书,那些几乎没有爱过的朋友,那些几乎没有游览过的城市,那些几乎没有占有过的女人!我出于厌倦或出于消遣,有过一些行动。人们跟着,他们想依附,然而一无所有,而这就是不幸。那是对他们来说。因为对我来说,我已经忘了。我从来只记着我自己。
至少,我知道只有在罪人以及被告的罪过对我毫无损害时,我才站在他们一边。他们的犯罪使我雄辩,因为我并不身受其害。当我受到威胁时,我不仅变成法官,更有甚者,变成一个狂暴的主人,要不顾一切法律,痛责罪人,使其屈服。在此之后,我亲爱的同胞,就很难再郑重其事地认为自己有奉行正义的使命,充当孤儿寡妇的天然保护者了。
根据这一观点,经过了青年时代不可避免的麻烦之后,我很快就打定主意:好色,我的爱情生活唯有它才存在。我只是寻求作乐和征服的对象。我的体格帮了我的忙,自然待我不薄。我对此颇感自豪,我得到很大的满足,简直不知道该说是感官的满足还是威望的满足。
事实上,我们的女友们与波拿巴有共同之处,她们总是想在别人都失败的地方成功。
赢了,而且是双重的胜利,因为除了我对她们的欲望之外,我还每次都通过检验我的魅力而满足了我对自己的爱。
一些男人喊:“爱我吧!”另一些则喊:“别爱我吧!”但是,某种最坏的、最卑劣的人说:“别爱我,但要忠于我!”
爱的举动,比方说,是一种供词。其中自私在大喊大叫、明目张胆,虚荣则昭然若揭,或者真正的仁慈也在其中显露出来。
没有一个人在寻欢作乐中是虚伪的,
不,当我面临被抛弃的危险时,唤醒我的不是爱情,也不是仁慈,而仅仅是希望被爱,得到据我看来属于我的东西。我一被人爱上,而我的相好重又被我忘却,我就高兴,我就舒服,我就变得讨人喜欢。
人们不能希望所有的人都去死,无论如何,也不能为了享受一种非如此不能想象的自由而使地球灭绝人迹。我的感觉反对,我对人的爱也反对。
只有您的死,才能使人们相信您的理智、真诚和您的痛苦之沉重。只要您一息尚存,您的情况就可疑,您就只能受他们怀疑。
我爱生活,这是我唯一的弱点。我是那样地热爱它,对此外的一切毫无想象力。这样的渴望有种平民味儿,您不觉得吗?贵族总是稍稍离开本人,离开本人的生活来想象自己。需要死的时候去死,宁折不弯。我呢,我弯,因为我还继续爱我自己。
自从我悟出我身上有可以受审的地方之后,我终于明白了,在他们身上有一种不可抵抗的审判别人的倾向。
要么因幸福而被审判,或是被免诉而悲惨。
于是,人们为了自己不被审判,就匆匆忙忙地审判别人。有什么办法?人类最自然的念头,天真地出现的,犹如来自他本性的深处,是他自己的无辜。
我们都是特殊情况。我们都求救于某种事情。每个人都宣称无辜,不惜一切代价,甚至为此而指控人类和上苍
我们很少信任比我们好的人,这可太真实了。我们宁肯避免与他们往来。相反,最为经常的是我们对和我们相似、和我们有着共同弱点的人吐露心迹。因此,我们并不希望改掉我们的弱点,也不希望变得更好,我们大概首先应该被判犯了错误。我们只是希望在我们的道路上受到怜悯和鼓励。一句话,我们希望不再有罪,同时对自己的纯洁不作努力。不要够多的无耻,也不要够多的道德。我们既无力作恶亦无力为善。您知道但丁吗?真的?见鬼。那您知道但丁在上帝和撒旦的争执中接受了中立的天使。他把他们置于不确定的地带,在他的地狱的某种前厅里。亲爱的朋友,我们正在这前厅里。
虚心佐我闪光,谦卑助我制胜,德行辅我压迫。我通过和平的手段进行战争,最后通过无私的手段获得了我觊觎的一切。比方说,我从不抱怨人家忘了我的生日,人家甚至怀有一种钦佩之情对我关于此事的缄默感到惊讶。然而,我的无私之原因却更不引人注目:我想被人忘却,以便我能够自怨自艾。
我被迫掩盖我生活的罪恶部分,使我装出一副冷淡的、人们常常混同于德行的那种神气,我的冷漠使人们爱我,我的自私在我的慷慨大度中达到顶点。
我得出结论,我精于轻蔑。那些我最常帮助的人,是最受轻蔑的人。彬彬有礼地、怀着充满激情的友爱,我每天都往所有的盲人脸上吐唾沫。
您记住:“当所有的人都说您的好话时,您就倒霉了!”
事实上,一种可笑的恐惧追逐着我:人不能不招供他所有的谎言就死去。
那时候,我真觉得我需要爱情了。下流,是不是?反正我感到一种暗暗的痛苦,某种使我变得更加空虚的匮乏,它使我半是被迫、半是好奇地承担某些义务。既然我需要爱和被爱,那我就认为自己陷入了爱情。换句话说,我装傻。
我很知道人们离不了统治别人和被别人服侍。每个人都需要奴隶,如同需要纯洁的空气一样。统治,就是呼吸,您同意这个观点吗?甚至命运最不济的人也能够呼吸。社会阶梯最底层的人还有其配偶和孩子呢。如果他是光棍,他还有条狗。一句话,能够发怒而另一个不能顶撞,这是根本的。“人不能顶撞他父亲”,您知道这句话吗?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句话不可解释。在这个世界上,不顶撞他爱的人顶撞谁呢?但是从另一种意义上说,它又是令人信服的。应该由一个人说了算。否则,任何一种道理都可以有另一种道理与之对立,这样就会没完没了。相反,实力解决一切。我们花了时间,明白了这一点。例如,您该注意到,我们古老的欧洲终于用正确的方法来推究问题了。我们不再像幼稚时代那样说:“我这样想。您如何反驳?”我们表达得清晰了。我们用通告代替了对话。“这就是真理,我们说,你们尽可以讨论,这我们不感兴趣。但是,几年以后,将有警察,它将向你们表明我有理。”
每一种过度的行为都削弱生命力,因而也减轻了痛苦。
我们不能肯定任何人的无辜,却可以肯定一切人的罪状。每个人都是他人的罪行的见证。
别等末日审判了。它每天都在进行。
谋害一个人总是有理由的。相反,却不能为他活着找出理由。
人们能够在这世界上进行战争,装作去爱,折磨他的同类,在报纸上自我炫耀,或只是一边打毛衣一边说说邻居的坏话。然而,在某些情况下,继续下去,仅仅是继续下去,那就已是超人的事。
人们不宣告任何人无罪。无辜已经死去,法官泛滥成灾,各式各样的法官,基督教的,反基督教的,他们是一丘之貉,在难受牢房上妥协了。
从此,既然我们都是法官,我们在彼此面前就都有罪,我们都以卑鄙的方式当基督,一个一个地被钉上十字架,而总是不明白。
人类最高的痛苦是没有法律而被审判。
您看,与我接近的一个人将人分为三等:喜欢无可隐瞒胜于被迫说谎者,喜欢被迫说谎胜于无可隐瞒者,同时喜欢说谎和隐私者。
谎言最后不也通向真理吗?而我的故事,或真或假,不是都朝着同样的结局、具有同样的意义吗?如果在两种情况下,它们都表明了我过去是什么人,现在是什么人,它们是真是假又有何妨呢?有时候,人们看一个说谎的比看一个说真话的还要清楚呢。真相,如同光亮,炫人眼目。谎言则相反,是一抹美丽的霞光,它使每样东西都显出价值。随您怎么看,反正我曾在一个俘虏营里被委任为教皇。
我不知道自由原来不是一种奖赏,也不是一枚人们喝香槟酒来祝贺的勋章。它不是一件礼物,也不是一盒能给您口腹之乐的甜食。啊!不,相反地,那是一种苦役,一次长跑,极为孤独,令人精疲力竭。
任何一种自由后面都有一篇判词;这就是为什么自由太沉重了,担负不了,尤其是在发烧、受苦,或不爱任何人的时候。
最根本的是不再自由,是怀着悔恨之心服从比自己更为狡黠的人。当我们都是罪人的时候,那就是民主了。
既然人不审判自己就不能判决别人,那就得自己攻击自己以获得审判别人的权力。既然任何一位法官有朝一日都得成为忏悔者,那就应该走相反的路,当忏悔者,以便能够最后成为法官。
我越是认罪,我越是有权审判你们。更有甚者,我激起你们自己审判自己,这使我感到轻松。
实际上我错了,不该对您说最根本的是避免审判。最根本的是能够为所欲为,哪怕不时地大声宣扬自己的卑鄙。我重又为所欲为,这一次没有笑声了。我没有改变生活,我继续爱自己,利用别人。只是我忏悔过失使我得以更轻松地重新开始,得以享受两次,先是我的天性,其次是迷人的悔恨。
我们失去了光明,失去了早晨,失去了那个自我原谅的人的纯真。
©暴躁的萨蒙
长按下方二维码关注我
感谢阅读,
祝你快乐。
作者
暴躁的萨蒙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帕布莉卡 » 加缪《堕落》读书笔记——从莫尔索到克拉芒斯
 帕布莉卡
帕布莉卡


 爱是一颗心遇到另一颗心(出处+配图)
爱是一颗心遇到另一颗心(出处+配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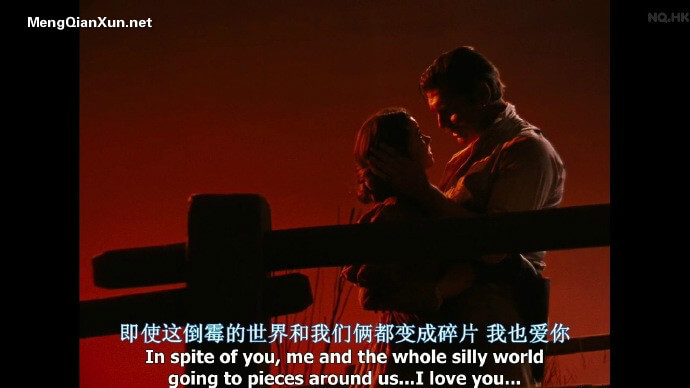 《乱世佳人》电影专题
《乱世佳人》电影专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