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晚睡前,静静地躺在床上看几页《冬牧场》,跟着李娟一起进入零下三四十度的冬天,放羊、背雪、喝茶、吃馕……凛冽的寒气透过文字扑面而来,小小的卧室显得尤为温暖。
2010至2011年的冬天,李娟跟随牧民居麻一家进入新疆阿勒泰地区南部的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中生活了三个多月。正如自序中所言,这本书“记录的是一个漫长的冬天……可能我逼真还原了那个冬天的所有寒冷。但寒冷并不是全部,我还以更多的耐心展示了这寒冷的反面。那就是人类在这种巨大寒冷中,在无际的荒野和漫长的冬天中,用双手撑开的一小团温暖与安宁。虽然微弱,却足够与之抗衡。这本书可能感动了很多人,但我觉得最大的感动来自于我自己,我最受感动。”
书 摘
在阿克哈拉村,我实在是个扑朔迷离的人物。主要有四大疑点:一、不结婚;二、不工作;三、不串门;四、不体面。
所谓“冬窝子”,不是指具体的某一个地方,而是游牧民族所有的冬季放牧区。从乌伦古河以南广阔的南戈壁,一直到天山北部的沙漠边缘,冬窝子无处不在。
一个人牵着驼队,孤独、微弱地走在沙漠中,整面大地空空荡荡,天似穹庐,唯一的云停在天空正中央。那是一团台阶状的梯云。前后无人,四顾茫茫……那感觉既非凄凉也非激越,说不出的怅然,又沉静。千百年来,有多少牧人以同样的心情孤独地经过同一片大地啊。
传说中最好的牧场是这样的:那里“奶水像河一样流淌,云雀在绵羊身上筑巢孵卵”——充分的和平与丰饶。而现实中更多的却是荒凉和贫瘠,寂寞和无助。
在这个地窝子里,每天早上,每一个人都依恋着热被窝。嫂子早已生起了炉子,烧好了茶。她一遍一遍地唤父女俩起床,可谁也叫不答应。她叹口气,只好也钻进居麻的被窝躺下来。另一边的加玛也离开自己的被窝硬凑了进去,三个人挤得紧紧的。居麻没办法,只好起来,一边穿衣,一边嘟囔着“坏女孩”、“坏老婆子”。而到了晚上,已经很晚了,谁也不愿立刻睡觉。就着昏黄的太阳能灯泡,加玛绣花,居麻为大家朗读旧的哈文报纸,嫂子捻羊毛线,我看书、做笔记,小猫东扑西颠,练习捉老鼠。茶壶在铁炉子上咕嘟嘟响了很久很久以后,居麻叹口气:“喝茶吧。”嫂子便放下手里的活计,铺开餐巾摆开碗,大家围坐一圈静静地喝茶。
这些羊都记得吗?宰杀它的人,又能有什么仇恨和恶意呢?大约生命的事情就是这样的吧:终究各归其途,只要安心就好。
我喜欢的哈萨克作家叶尔克西姐姐提到过,宰羊之前的那句巴塔大致意思是:你不因有罪而死,我们不为挨饿而生。
在野外拍照时,看到镜头上蒙了点尘土,便习惯性地吹了一口气。结果水汽立刻凝结在镜头上,结结实实地冻成白色的冰霜。接着越擦越模糊。
总算明白了为什么古人会说“酸风射眸子”——果然很酸!果然是“射”!迎风眺望远方,不到几秒钟就泪流满面,眼睛生痛。加上眼泪在冷空气中蒸腾,雾气很快糊满镜片,又很快凝固为冰凌,眼前立刻什么也看不清了。而这风明明又不是什么大风,只比微风大了一点点而已。
显然居麻对自己的婚姻还是极满意的,叹道:“要是过得不好,早就离婚啦!”接下来,向我列举了村里一些刚结婚就离婚的夫妻,以及一些结婚多年了又离掉的——“唉,现在的人,脾气越来越大了!”说完,扑在嫂子怀里,用抽咽的声音撒娇道:“这么好的老婆子,给我生了四个娃娃的老婆子……呜呜……”嫂子一手抚摸着他的头,一手持碗继续喝茶,不为所动。快要离开这个家庭时,我挑一个光线柔和的黄昏给这夫妻俩好好地拍了几张照片。看照片时,居麻沉重地说:“我明明站在这边,你嫂子的头为啥要往那边偏?可能不喜欢我了……”
大家吃雪的时候,牛伸出舌头转着圈地舔;马老老实实龇出牙去啃;骆驼最厉害,垂下长长的脖子,下巴平贴地面,像开铲车一样平铲过去,一下子就能铲满满一嘴,再合上嘴一口吞掉。我猜骆驼的祖先可能有铲齿象的基因。
羊的个子太矮,难免目光短浅。当羊群整体移动时,中间的羊永远也搞不清状况,只知跟着瞎走。只有走在边缘的羊才能看清周遭形势。尽管如此,边缘的羊还是边走边想方设法往羊群深处挤。大家都愿意盲从,好像世上最安全的事就是让自己消失在“多数”之中。
我这人,啥都怕,就是不怕闲。“闲”这个东西,真是再多也不够用的。
不过,此时热烈的歌唱和欢声笑语也像是在深深的井底。门外黄沙滚滚,寒冷无边。一家人紧紧围绕着小火炉,欢笑着,吵闹着,这欢乐和吵闹多么孤独,孩子们的成长多么专注、无扰。
刚进入荒野时,月亮在我眼里是皎洁优雅的。没多久,就变成了金黄酥脆的,而且还烙得恰到火候……就更别提其他一切能放进嘴里、吞进肚子里的东西了。面对它们,我像被枪瞄准了一样动弹不得。
到了今天,恐怕只有在荒野里,在刀斧直接劈削开来的简单生活中,食物才只是食物吧——既不是装饰物,也不是消遣物。它就在那儿,在餐布上,在盘子里。它与你之间,由两点间最近的直线相连接。它总共只有一个意味:吃吧!——食物出现在口腔里,就像爱情出现在青春里。再合理不过,再美满不过了。
问题:什么样的食物最美味?答案:简单寂静的生活中的食物最美味。在简单寂静的生活里,连一小把炒熟的碎麦子都香得直灌天庭。把这样的碎麦子泡进奶茶,再拌上黄油——全身心都为之投降!……那是怎样的美味啊,每细细咀嚼一下,幸福感的浪潮就席卷一遍身体的沙滩,将沙滩上的所有琐碎脚印抹得一干二净。
如果热茶里添加的是一把“阿克热木切克”(变质的牛奶制作的奶酪)末儿,则更有嚼头了。面对那香气,如面对体重一百二十公斤的妇人——她殷勤地站在那里,温和又稳当。如果这茶里还煮进了丁香粒和黑胡椒,那妇人便意味深长地笑了。
拉面的存在只有一个目标:把肚子撑圆了!
麦子粥则像熨斗一样把肠胃拾掇得服服帖帖。如果是加了酸奶糊的羊肉汤麦子粥,则会令肠胃里所有的消化酶拉起横幅,列队欢呼。
吃包子时,世上最好吃的东西是包子。吃抓肉时,世上最好吃的东西又变成了抓肉。这两种结论毫无冲突。
想想包子馅吧:土豆粒、肉粒、油渣。再想一想:沙沙糯糯的土豆泥、汁水盈旺的肉粒、金黄的油渣……然后再想想抓肉,想想居麻飞快地做完餐前巴塔(简单得几乎等于没做)后操起小刀就开始削肉,想想肉片下晶莹的面片饱饱地吸足了肉汤,暗自得意,欲要和肉片一较高低……包子也罢,抓肉也罢,哪怕吃得撑到了嗓子眼,仍感觉还能继续再吃。
做包子剩下的馅还接着做包子吗?不!嫂子创意多多。第二天她又剁了些肥肉加进去,再擀两块方向盘一样大的圆面饼,夹住肉馅,四面捏紧,像烤馕一样丢进滚烫的羊粪灰烬里烘烤……多么隆重的烤包子啊,方向盘一样大!等待包子出炉的时间里,大家团团围坐。邻居家两个孩子说什么也不离开,无限地耐心。这个方向盘般的大包子一端上餐布,其光辉便照亮了整个地窝子。嫂子像切生日蛋糕那样切开它,油汁四溢。热合买得罕眼明手快,占据了最大的一块饼,斯文地慢慢吃,再斯文地拒绝第二块。
还有羊粪灰烤的薄馕——嫂子先烧起一大堆羊粪,等充分燃烧完毕,把剩下的滚烫细腻的灰烬扒开,摊平。再把事先揉好的面团擀成一大片面饼,不垫任何器具,直接投入灰烬之中。然后把四周的粪灰聚拢过来,完全埋盖住这块洁白的面饼。等灰烬完全降温后,扒出金黄、瓷硬的面饼——哎哟,香得哟……叫我说什么好呢?
而加玛最感人的魔术是突然从铁皮炉里的羊粪灰烬中刨出一颗土豆。哎哟,多么奢侈啊!我俩一人掰一半分吃了。掰开的一瞬间,沙沙的土豆瓤里呼地冒出一团热气,把冬天都融缺了一个小角……
天空下最大的静不是空旷的静,不是岁月的静,而是人的静啊。人终究是孤独而又无法泯灭希望的……
知道得越来越多时,会发现不知道的也正在越来越多。这“知道”和“不知道”一起滋长。这世界从两边向我打开。当我以为世界是籽核时,其实世界是苹果;我以为世界是苹果时,其实世界是苹果树;我以为世界是苹果树,但举目四望——四面八方无边无际的苹果树的森林……
无论如何,生命需要保障,世人都需要平等地受用现代生活。一定要定居,羊群一定要停止下来。不只是牧人,连大地也承受不了了。羊多草少、超载过牧的状况令脆弱的环境正在迅速恶化。
居麻躺在床榻正中央抽烟。加玛枕着他的膝盖,大声念一份哈文报纸。嫂子则从另一侧躺在他怀里,蜷着身子认真地听,眼睛明亮无比。居麻被两个女人环绕着,也十分享受。如果有烟灰落在嫂子头上,就轻轻为她掸去。地窝子外,大风呼啸,天窗哗哗作响。似乎有人在风里努力大喊:息怒吧,请息怒!
我说:“扎达长大了,结婚了,生下的第一个孩子你们会要吗?”——长孙过继为幼子,这是哈萨克古老的礼性。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帕布莉卡 » 【书摘】李娟《冬牧场》
 帕布莉卡
帕布莉卡


 爱是一颗心遇到另一颗心(出处+配图)
爱是一颗心遇到另一颗心(出处+配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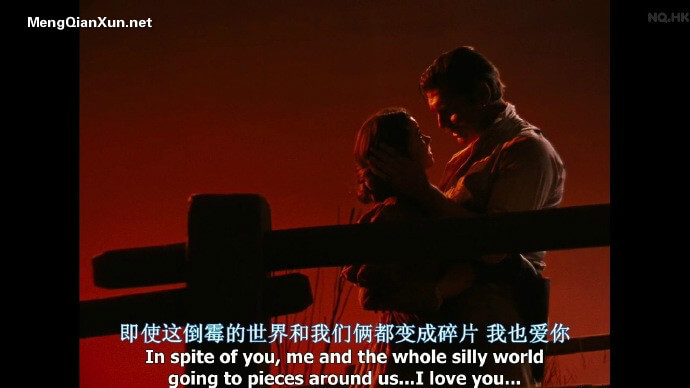 《乱世佳人》电影专题
《乱世佳人》电影专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