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李卓然 读名著学套路
忆昔午桥桥上饮,座中多是豪英,长沟流月去无声,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
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闲登小阁看新晴,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更。
1971年出版的《台北人》,是白先勇先生集结之前数年创作而成的一部小说集。这是一本深具复杂性的作品。此书由十四个短篇小说构成,虽然写作技巧和写作手法各异,长短也不尽相同,每篇单列出来皆可称之为精品,但是这些篇目整合在一起却陡生更加深邃的内涵。
这十四篇作品为读者勾勒出随国民政府退居台湾的“大陆人们”及其后裔在台北定居多年后的众生相,让我们看到了一群漂泊在异乡的游子们的孤独与挣扎。这种孤独和挣扎不仅体现在现实生活中的贫瘠和残酷,更多的是精神上的折磨和无处安放。
作品中的主人公,无论是上流人物中年迈挺拔的儒将朴公(《梁父吟》)、窦夫人(《游园惊梦》)、社交界名女尹雪艳(《永远的尹雪艳》)还是下层社会里的“总司令”(《孤恋花》)、退休女仆顺恩嫂(《思旧赋》)、国军老兵赖鸣升(《岁除》),他们来自中国大陆不同的地域,他们地位悬殊,身份各异,但是却都背负着一段沉重的、剪不断斩不去的过去,这些过去都与“民国”的历史和“大陆”的土地深深的嵌合在了一起,鱼水交融,难以忘记,却都因那个“忧患重重的时代”而被强行的割裂开。
他们的光荣的难以忘记的过去都与中华民国的兴衰荣辱相关。夏志清先生说:“《台北人》甚至可以说是部民国史,因为《梁父吟》中的主角在辛亥革命时就有一度显赫的历史”。民国成立之后的重要历史事件我们好像都能在书中找到:辛亥革命(《梁父吟》)、五四运动(《冬夜》)、北伐(《岁除》)、抗日(《秋思》)、国共内战(《一把青》)。在最后一篇《国葬》中的李浩然将军,则集中华民国的历史于一身:桓桓上将。时维鹰扬。致身革命。韬略堂堂。北伐云从。帷幄疆场。同仇抗日。筹笔赞扬。从小说里李浩然的身上我仿佛能够看到白崇禧的影子,难怪白先勇先生在首页会提上:纪念先父母以及他们那个忧患重重的时代。
时代变化了,国内外的空气也阴晴无定,历史的车轮终于碾过那些个岁月,然后让这些时光像凝固了的雕塑一样弃置在落了灰的角落。可是那些从彼处而来的人们依然还跳动着生命的脉搏,他们的生命被困禁在了那个“孤岛”上,却将灿烂的青春和美好的回忆永恒的留在了永远无法归去的故土。因而这些“台北人”不仅仅是历史的见证者,同样也是历史创伤的深切体会者。在他们的痛苦中,除了政治上带来的“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还有文化上的隔膜和痛楚。“外省人”和“本省人”的生活、文化差异;中国旧式单纯、讲究秩序、以人情为主的农业社会和现代复杂的,以利害关系为重的、追求物质享受的工商业文明之间的冲突;年轻一代出生在台湾的青年男女,没曾亲眼见到国家兴衰,未曾亲身体验人生悲欢的时代隔阂。余秋雨称之为“世纪性的文化乡愁”。将浓浓的文化乡愁通过象征的途径渗透到《台北人》的每篇作品中,以宏大的历史感使这种乡愁也气势夺人、含义深厚,因而可称之为世纪性的文化乡愁。
白先勇先生将他感受到的历史的苍凉感和面对历史的无力感糅杂进《台北人》每篇小说的枝枝蔓蔓里,从而表达出他的历史观——感叹时代兴亡的怅惘和感时伤怀的追悼。一个有着深厚中华文化传统的知识分子,将他精神世界中的“大我”(对于民族、文化和同胞的同情和怜悯)与“小我”(对于逝去青春年华的追忆)统一进了整部作品里。
他将刘禹锡的《乌衣巷》置于《台北人》的卷首:“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每次翻翻这本书,我脑子里常常能够想到曾经去南京时看到过的破败的乌衣巷,想象着它从前的辉煌。又想到总统府前的楹联:大堂深似海,长挟石城沧桑中山风雨;国史壮如彤,曾振辛亥鼙鼓己丑雷霆。继而想到于右任“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的恸哭,余光中“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的企盼,罗大佑“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的苍凉。
我们民族的这段历史已经渐渐的被我们自己遗忘了,就像《台北人》里的那些“外省人”的后裔。那些曾经的亚细亚孤儿们也已经渐渐老去,或步履蹒跚,或已经葬于高山之上兮了。于是《台北人》这样的作品就显得弥足珍贵,它让我们在习惯于遗忘的现代社会里能够有机会喘一口气,回望一下我们的同胞在那个忧患重重的时代里走过的岁月,那是他们的岁月,也是我们共同的历史。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帕布莉卡 » 亚细亚的孤儿们——《台北人》里的时代与众生相
 帕布莉卡
帕布莉卡


 爱是一颗心遇到另一颗心(出处+配图)
爱是一颗心遇到另一颗心(出处+配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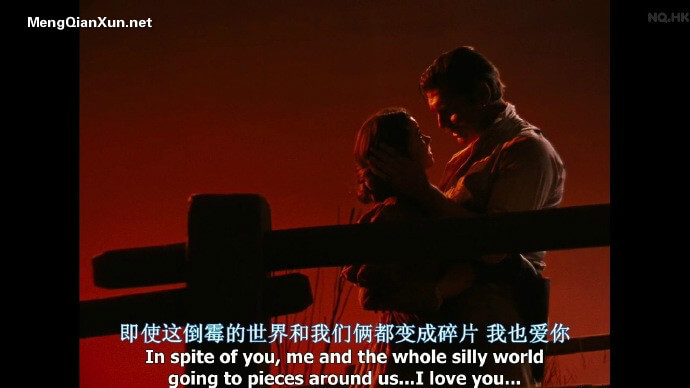 《乱世佳人》电影专题
《乱世佳人》电影专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