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不更新了,问候大家!开始是生病,感觉倦了累了,退出许多群,不再在群里说话。有时收到朋友的信息,像从遥远的世界带来,我会恍然发现,我们的生活是多么丰富、庞杂、琐碎又具体,我们彼此从文字了解的多么稀少,不足十分之一,甚是感叹!一段时间,我完完全全投入到生活工作之中,体验享受承受一切,感觉忙碌充实又完整,也轻松很多,不像以前偏执于文字。最近工作忙点,切切实实投在生活的大潮里,接触一些人,经历一些事,感受再感受,的确,就像林贤治老师说的,光看稿读书写作,会感觉生活在生活之外。我自己也是开放的,随时接受生活工作的邀请,让自己多看看、多了解,闲下来看书,过得还算充实,只是感觉这种日子比较容易过,也过得飞快,它们在心上留有印迹而未成形文字是有点遗憾的,一直想记下来又未动笔,我不知道以后怎么走,总之,这一段时间我懒散一些了,不过感觉心安理得的愉快。今天匆匆写了一点笔记,算是给自己和朋友们一个交待。
读《张枣的诗》
文|思
2021年1月17日的午后读完了这本《张枣的诗》,里面收录了一百多首,差不多是张枣一生在诗歌上的所有硕果。张枣因患肺癌,生命终止在48岁,的确是令人惋叹的英年早逝。
一百多首诗,阅读和记录花了22小时,张枣的诗不易懂,有晦涩难解之处,但只要从诗写角度入手,相信是越来越靠近他的。最重要的是,你和诗人在精神边远处有高度的契合,或对诗歌与文字表达有深深的领悟力(那相通的普遍性是公约数,就是一把打开锁的钥匙),让你能理解他,理解他的表达,理解他为何而写,为什么要那么写。常言道,作者也在寻找驾驭他的作品的猎手(大意),我庆幸,曾深入一位中国诗人的精神内核,打开它的意象的丰富内涵,打探过它们的虚实和可能象征,我随张枣的“鹤眼”飞翔飞翔,飞翔,祈望成为他,成为他的鹤,与他同一,见他所见,思他所思,深入理解他的作品,最后在他生于尘归于尘的人间着陆。我万分感激:诗歌是开放又隐蔽的场域,开放是说所有人可读,隐蔽是说它只向能理解它的人敞开。涉猎一位诗人的精神园地,即是艺术宝库的天赐和馈赠。
2010年3月,张枣在德国图宾根医院逝世后,曾与他相处三年的学生颜炼军多方搜集老师生前所有作品,编成了这本诗集,而“编后记”也写得感人肺腑,催人泪下,想来,颜炼军也是深得老师诗歌精神脉络承传的,否则我们读他写张枣的文字不会掬一捧眼泪。那个诗歌精神的高地,始终令人向往,令人仰望,让人不断去写去成就而靠近它……
印象深刻的,是“鹤”、“蝴蝶”和“云”的意象对张枣的特殊意义。
在张枣那里,有关蝴蝶的诗句,是与庄子的蝴蝶一脉相通的,比如在《大地之歌》里,蝴蝶是这样翩然入场的:“小学生的广播操,刹车,蝴蝶,突然归还原位:一切都似乎既在这儿,又在飞啊。”在《一个发廊的内部或远景》一诗里,有这样令人叫绝的关于蝴蝶的描述:“我睡在凉席上却醒在假石山边。蝴蝶携着未来,却重复明代的某一天。”短短两句里出现三个时空,现在、未来和明代,三个时空交汇,错乱,中国人一看即明了是庄子梦境里的蝴蝶变体,一点即通其象征意义。
“云”的意象对张枣的份量更不用说了,他专门写了一首《云》的组诗来谈它,我们说云朵轻灵,美丽,虚幻,有形而不实,正好可拿来表示心的幻象,尤其对身处德国异乡的张枣来说,在国内经历的物事人是触摸不及的云朵,而诗歌的空幻也有类似性质,这朵云却也是救赎张枣的云:
“当我,头颅盛满蔚蓝的蘑菇,了望着善的行程,儿子,别说云里有个父亲,云朵的几只梨儿摆在碗中,这静物的某一日。…这是中午,或者说,这是虚空,谁也拿它没法。这是你的生日;祈祷在碗边叠了只小船。我站在这儿,而那俄底修斯还漂在海上。在你身上,我继续等着我。”
这首诗最能体现张枣在异乡飘泊的感受,他把自己比作特洛伊战争后,在海上飘泊十年,同伴海难,而自己历经重重困难,倍受孤独折磨最后得以返乡,谋计杀死众多仇敌的俄底修斯。而诗人不是已然衣锦还乡,他似乎还在远方向家乡作永远的眺望。张枣身处德国,常常夜半醒来,有迷糊之感,不知身居何处,人的整个存在被轻飘飘拔起。人的身份认同决定存在的感受,没有祖国与家乡的根系,人又靠什么来认定他自己呢?于是虚无之感肆掠。
张枣说:“这儿是哪?这是千里之外。离哪儿最近?很难说——也许,离远方。咫尺之外,远方是不是一盒午餐肉罐头,打开喂乌托邦?远方是漩涡的标本,有着筋骨的僻静,也有点儿讥诮,因为太远……远方是工具箱,被客人搁在台阶上,一朵云演出那遇刺的哑暴君,脸“啊”地一声走漏了表情。”
刺客及走漏的表情令人叫绝!诗人凭窗远眺,不断涌现,自我演绎一出出内心戏,以逃离和缓解寂寞深渊的大口吞噬……最终,这些戏仿的众多影子成了诗歌,成了挽救他的朋友。我们发现,即使临终前的绝笔之诗《灯笼镇》,张枣也能生出这种观者戏谑的戏仿之味,如临一场戏曲,还有合唱和画外音,仿佛是别人的葬礼和悲伤,这在诗歌内部烘托出一种更揪心的感觉,又仿佛一个人的死亡加入一场人间大戏而又有所安慰。
那么在张枣眼中,什么才是诗呢?诗人不会给出直接的定义,他用了一系列形象来说明,这也是诗人的擅长的技艺,比如张枣在《云》中如此回答这个问题:“下午一道回光伫立,问:你是谁?而没有哪种回答不会留个影子。这是诗艺。影子叠着影子使黑暗蠕动起来。尘埃,银河般聚成一股力,寄身于这光柱,奔腾又攀谈……”别问它象征着什么,“只因它不可见,瞳孔深处才溅出无穷无尽的蓝,那种让消逝者鞠躬的蓝。”诗歌让消逝重现,大概就是这样的大象无形的精神召唤吧。“让消逝者鞠躬的蓝”,这里的姿态蕴含品格、礼仪和高贵,只因人皆有一死,所以才会鞠躬,如此生花妙笔,让人恍然明白什么叫好诗好句!
生活的许多场景里,一遍一遍地,张枣恍然忘了自己的名姓,不知自己是谁,不知今夕何夕,只有庄周那只蝴蝶闪来闪去。异乡的孤独不治之症啊,常牵起他对自己身份的怀疑,升起与自我疏离的渺远之感。可以说,诗歌确证这感觉并让诗人寻找自己。
张枣在《一个发廊的内部或远景》一诗里写道:“你只要觉得孤独,你就该知道一切全错了,而且已无法更改。无风之际只有风突然逆着流水站起身来,像一个怒者,向前扑着,撕着纸,当你的真名如鸣蝉的急救车狂奔而来。”这思乡病,心理上,张枣无能为力而自责,似乎有些悔恨当初的离开,在《一个发廊的内部或远景》里,张枣把自己形容为“从北方畏罪潜逃的税务官”,或者说,所有离乡背井人们,都早已自动给了自己一张罚牌,对故土的怀念和亏欠,之前或有所意识,之后即是一遍遍确认撕裂的疼痛。
张枣病逝前所写,未被收录此诗集的《鹤君》,依稀留有这么几行在人间绝响:“别怕,学会躲到自己的死亡里去/在西边的西南角,靠右边一点儿……”西南,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他的故乡长沙,那么,我们可以想象,临终时,于异乡的诗人,手握的还是地球上一个具体而微的空空地址,那里承载着家乡和亲人、故土的怀念记忆,如此空洞,如此缈远,又因了情感,如此盛载丰富。
在接下来的《大地之歌》里,张枣再次言及想象与幻觉的重要性:“黄浦公园也是一种真实,没有幻觉的对位法我们就不能把握它。”我们得在它对面的电视塔为爱人塑一座雕像,“她失去的左乳,用一只闹钟来接替,她骄傲而高耸,洋溢着补天的意态。”这个女性雕像形象也可用来形容诗歌本身,补缺着我们用理性知识把握世界的先天不足。在《世界》一诗里,张枣一再重申不可见之物即心像的重要:“这个世界里还呈现另一个世界…是一个同时也是两个世界。因而我信赖那看不见的一切。”虽然这首诗是描写所爱的女孩披上嫁衣嫁作他人妇的失落,但空空的怀念和拥抱不失为一种补偿甜蜜的慰籍。
但也有相反的记忆失踪的情况。在《湘君》一诗里,描述的是事隔数十年,两位旧友喝咖啡叙旧,谈及少时生活,成长中共同接触的一些人在某人记忆里鲜活着,在另一个人心里却被全然遗忘,维系共同记忆的那人形同死亡,从未存在,共有的记忆线索彻底断裂,曾存在过的完全缺席,这简直荒谬,不仅是被遗忘的人死亡,还是我与朋友共同分享的经验的二次死亡,这未免不是人类互相寻找认同感觉的一大讽刺和悲哀,张枣说:“哪个?我在你脸上搜找着。我着急地问,我着急地望着咖啡杯底那些迭起如歌的漩涡,那些浩大烟波里从善如流的死者。”记忆的遗忘我们拿它如何是好呢?所以文学一直声称是对人类集体或私人记忆的一种见证和挽留,它复活我们记忆乏力的先天不足。
《到江南去》写得令人动容,是张枣写于1999赠予诗人钟鸣的诗。与钟鸣一次跨洋电话连线,没说上两句,突然电话断了,正在兴头上的谈话戛然中止,而张枣还想返回线路的通道中觅寻,枉然续上他的江南旧梦,他说:“对,到江南去!我看见那尽头外亮出十里荷花,南风折叠,它像一个道理,在阡陌上蹦着,向前扑着…时而急走,时而狂暴地抱住那奔进城的火车头,寻找幸福,用虚无的四肢。”荷花用虚无的四肢狂暴寻找,江南和幸福在远方的远方,这思乡病何等热烈,何等赤裸,又何等忧伤!
“电”这个字眼在张枣眼中也别具含义,比如在《大地之歌》里,他写道:“他们同样都不相信:这支笛子,这支给全城血库供电的笛子,它就是未来的关键。一切都得仰仗它。”“蝴蝶管制那么几瓦电,抖簌在标语上。”“电”表示“生之力”和“精神之力”吗?
“鹤”这个意象对张枣也有特殊意义。有逆着美军飞机闪亮飞翔的鹤,还有鹤之眼:“里面储存了多少张有待冲洗的底片啊!”(《大地之歌》)。前面已提过,张枣病逝前在儿子作业本上题了仅两行的未完成之作《鹤君》,由他生前好友宋琳和欧阳江河大致辨识出来:“别怕,学会躲到自己的死亡里去/在西边的西南角,靠右边一点儿……”据说张枣还有一首题为《鹤》的诗,因病重,只来得及留下模糊凌乱的句子。正如他的学生颜练军在编后记里所说:“张枣留下的一百多首诗歌,绵绵不绝地发出风声鹤唳。它们搅动了各种回顾和愿景,修改着诗人之鹤的秘密行程,勾勒和引诱出更多微茫的飞翔和跌落。”鹤的意象的确贯穿了张枣的诗行,而诗即是一个诗人精神生命的翔舞。
《看不见的鸦片战争》写得极具吸引力,充满戏剧性,是张枣一贯拿捏得十分到位,他擅长的历史题材的想象发挥,意象非常丰富。大英帝国蓄谋已久,即将入侵大清,道光皇帝浑然不觉,因为弄臣们欺上瞒下,只谈月牙儿、玉环和小儿,千年铁树开花,西风袭来,天上的云朵陈列着异象,千军万马嘚嘚嘶鸣,都是不详之兆,举国上下还一片云淡风轻、闲云野鹤,一派假祥和,后来大清的措手不及,战败后,签订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南京条约》的结局是可想而知了。这首诗借一个弄臣的滑稽形象来衬托严肃国事的儿戏化真是举轻若重啊!
《灯笼镇》是患肺癌的张枣于2010年1月写的最后一首绝笔诗,仍然有点晦涩难懂。但他在诗中最后一节提到了“老虎衔起雕像,朝最后的林中逝去,雕像披着黄昏,像披着自己的肺腑,灯笼镇,灯笼镇,不想呼吸”,想来雕塑披着肺腑、不想呼吸等字眼,都是与肺病相关的凶兆,是身体意识的异感反应,张枣嗜好吸烟,十分厉害,至于被众所弃的“灯笼镇”象征什么,是肺叶癌变的标志吗?是有点引咎自取的失败人生?还是别的什么?得读者自个儿去琢磨了。为什么张枣用了戏仿形式呢?当然,我理解为诗人不想写成一场私人病痛,他想延展为所有人类会轻视自己并犯错的悲剧,通过自嘲,戏剧化无疑是极好的且富于反思意义的选择。
本诗集还辑录了六首张枣的早期诗歌,在这些早期诗里,我们仍然发现一个诗人令人惊叹的出色想象力和语言组织能力。有《赶路的风》、《影》、《雪》,《给一颗无邪的心》、《石头》似是十多岁的张枣恋爱和失恋的情诗,《寻觅》表达成长中的忧伤和失落。相对后期的纯熟诗艺,早期诗相对直白,感情浓烈或奇幻的想象力,均有可圈可点之处。比如,他将喜爱的白雪与太阳凝固一异想画面,作了对比:“…到哪儿去寻找生命憔悴的旋律?假如,太阳有一天会蓦然落地,那么就让白雪把他凝成一枚铜币。”表达炙烈情感而后寂灭的感觉::“火——心灵五彩缤纷的苦果,以阳春鲜艳的肉体为燃料…寻找火——那在成熟的黑暗里所孕育的、所失去的。”
张枣1993年写的组诗《空白练习曲》让人读得不知所云,仿佛只是字词失序的群魔乱舞。只有少量句子能读懂,像一种情绪的骚动,不满和吐纳。我们会有理由怀疑:不知道那时流行的风格是什么,看不出大部分无厘头的字词组合有什么意义,如果诗歌语言不传达意思,或声音带来的乐感,那是否这些诗只表明心智和精神本身为反叛而反叛,一种形式主义。好像诗人在自创语言,甚至连呓语都不是,呓语至少语序是可把握的,属于“常规语言” ,我们还能解密,结合精神分析去理解,但这个组诗只是像一条鱼儿吐了一长串泡泡,好像只是有意表明“我说,所以我存在”、或者“我存在,所以我说”,亦或“我存在并说”,只是单纯的要发声而已,又或者,一个人如孩子般的叫喊了一气:“喏,看,我在这儿,我照镜子,我挤眉弄眼,别问我镜子是什么,以及镜子于我的意义……”或者,诗如题目一般,就是空白练习曲嘛,空白……练习……就像小孩玩填字游戏,玩完就算了,你从中苦苦觅寻什么呢?不是多此一举吗?我大致领悟这首诗总的感觉好像说社会氛围的一种虚伪,以及一个诗人在做的语言实验。我们不要忘了,对于诗人,精神语言的创新表达任务,一直是驱策他们前进的动力。
正如诗人奥登认为:“读者对一首诗有两个要求。首先,它必须是做工精致的词语造物,并以此为他使用的语言增添光彩。其次,必须对我们大家公有的事实从一个独特的视点去理解,并说出某些有意义的话。诗人所说的话是此前从未被说过的,但是,一旦诗人说出了它,读者就会意识到对他们是有效的。”布罗茨基补充说:“似乎艺术奋斗的目标是致力于精确,而不是向我们说谎,因为它的基本法则毋庸置疑地坚持细节的独立。”正如大家共知的,张枣的作品从诗歌的抒情源头上继承了“风、骚”传统,是传统诗歌与现代诗歌的完美结合。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张枣用古典的中式意象,结合西式的精神表达,树立了语言别开生面的标杆,指引后代的诗人依循向前,不断在语言艺术上创造翻新,所以从上面两方面来评说“张枣是一位好诗人”绝不为过。
2021/01/17
(以上来自网络)
歡迎關注,思的公眾號
(点顶上“思说诗说”蓝字关注)
作者簡介:思
左手握文字,右手握生活,並時常被兩者拋棄和接納,她不想過多言說自己,更相信日色賜福予生命的公允,她的夢與你日日夜夜寓居的夢交纏、共生,並沒有太大不同。
 帕布莉卡
帕布莉卡


 爱是一颗心遇到另一颗心(出处+配图)
爱是一颗心遇到另一颗心(出处+配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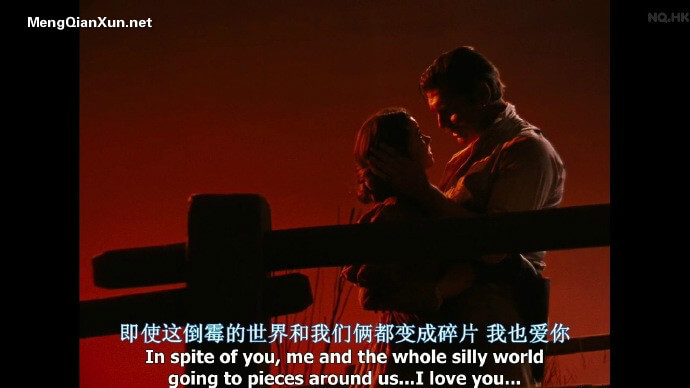 《乱世佳人》电影专题
《乱世佳人》电影专题

